今天,于可远头一次尝到被一个通政使司官员盘问的滋味,说实话,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一切都发生在翰林院的大堂,这间明明很光亮宽敞的大堂,现在却显得晦暗又狭小。这群人虽然都站在各自的大案前,或者坐着,但大多数人的目光并不望向翰林学士杨百芳,而是望向他自己,仿佛他把手伸进别人饭盒被当场抓住时的感觉。这都是赵贞吉搞的鬼!大案的一边坐着大约九个官员,中间便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忠。于可远看到他时就有些苦恼,来的为何不是右都御史胡文远呢?那事情是不是就简单许多?马文忠左边的是通政使司和翰林院的几位大人,右边是国子监和另外几位御史。稍下面一些是一个书办,负责会议记录。还有一些座位是给前来旁听的公公坐的。每个官员获准有下属陪同。因而于可远便让钱景陪在自己身旁,当然坐在他身后面一点,还加上张余德所谓的精神援助,嗯,没有用的口头话罢了。马文忠要求各部衙做开场陈述。第一个就是翰林院,而杨百芳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后,就将矛头指向自己,很明显这些人都串通一气了。于可远的作业做得相当不错,他将钱景在密轴里讲述的内容全都复述了一遍:诸如翰林院以高效率的标准运转,并确确实实在支持和服务其他部衙的文书工作。接着马文忠又问到詹士府的一些差使。他照例按照钱景所写的回答,很尽心,很称职。通政使司的那位左通政刘茂开始发问了。他轻轻咳嗽两声,似乎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其实他的身份已经足够引起旁人的注意力——为数不多的赵贞吉的支持者,这多有趣!然后他问于可远,是否认识张邕。听过,但没见过。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曾听闻。”于可远这样说了。若比官职,这个左通政品级还没有自己高呢,但到底实权更大,所以二人便以平级论了。他继续向于可远说,张邕是詹士府的一名小官。于可远告诉他,詹士府有五百多名官员,不可能指望自己全认识。这时刘茂声调拔高了,其实是大声压过了于可远,并且说这个人是被其他官员弹劾,然后罢黜了,后来回到老家还写了几首诗。嗯,怀才不遇随便写点诗词,这不是很正常吗?刘茂冲着于可远挥着一叠纸。“这是那几首诗词,每首都触目惊心!”他说道,同时扫了一眼公公的位置,“这个张邕在诗词中对朝廷,尤其是对你们詹士府挥霍朝廷公款的情况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指控!”于可远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詹士府并非只有他一个官员,但今天到场的只有他自己,谁让他身兼数职呢?他转向钱景,“你知道这回事吗?”钱景说:“属下并不知道张邕作诗这回事。”然后他小声念叨着,“真是意外,真是意外之祸啊!”这还真是让他充满信心。于可远继续问钱景,这个人是谁。“他就是个捣乱的,大人。”钱景说。意思是,这个人不明事理,这几乎是最大限度的辱骂了。于可远显然比钱景要不了解这个张邕,他问诗里都写了什么。“属下不知。”于可远渐渐冷静下来。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拖延。”钱景也忽然提到这个主张,真是大有帮助。他总要说点什么。“拖延?”他轻轻在心底念叨着,这话的意思就是避免回答。但他依旧有些恼火,努力忍住火气,但并不完全奏效。这就像是被送进了暴风骤雨里,连把雨伞都不给,亏他是自己信赖的下属!这时刘茂在叫他了。这样正好,否则的话,恐怕这个钱景就没法活着讲这件事了,开玩笑地说。“你和你的属下商量够了吗?于大人。”刘茂问。“十二分够了。”于可远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刘茂朝着马文忠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说:“让我给你读一读他这首诗里面揭发的令人发指的事实。”然后刘茂就念出了下面这句话,当然是翻译过的:“嘉靖三十六年四月,詹士府遗弃一座废弃仓库,仅用于堆砌物品,冬季却仍旧日夜以炭火供暖,每日维护费用八十两。嘉靖三十七年八月,詹士府送往裕王府的日常所需,名单记录价值二十万两,实际送达不足三万两,同日送往景王府日常所需,名单记录价值二十万两,实际送达超过五十万两。对此,于大人有什么话要说的?”自然,对此于可远绝对无话可说。他指出,如果不做出事先了解,他是不可能回答这种具体问题的。这是为官的严谨性,谁知道这个张邕是在撒谎还是喝醉了酒?刘茂不得不认可这个理由,但他声称自己质疑的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于大人,我问的是,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浪费和篡改,你还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解释?”于可远沉默着。这时马文忠似乎认为他应该回答。于是于可远尝试回答了一番,“或许有些东西,在低温下不能保存,所以詹士府才会日夜以炭火保温。这应该取决于里面储存着什么。”于可远的话正中刘茂的下怀。“一些铜线。”他立即说,然后笑了。满堂的官员也都在笑。“所以……”于可远又琢磨是不是有别的理由,“铜线在潮湿环境下,会被腐蚀,难道不是吗?”“都是上锈的,无法继续使用的铜线!”他说,继续等着。“原来是已经上锈的,”于可远点点头,“是这样啊,”他们似乎还想让自己说点什么,“多谢刘大人告知,我会调查此事的。”他主动提出。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寄希望于事情到此为止了。但是没有,其实这只是刚刚开始。“张邕还在诗词中写到,说你们詹士府集中购买日常所需的笔墨纸砚等物,然后按照个人的申请分发下来。”“这在我看来,是很合理的。”于可远谨慎地回答,并察觉到这是个陷阱,“毕竟大批量购买能够节约一些成本。”果然是个陷阱。“但张邕却说,”刘茂继续说,声调越发冷厉,“这一过程却比一些官员自己去大街上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贵十倍有余!”他原本想说,可以用详细的数字来证明这些事情,但想想还是放弃了。看得出来,这位刘茂刘大人,乃至马文忠大人,若非掌握着某种确凿的证据,不会如此断言。而且以他在詹士府,不仅仅是詹士府,包括翰林院和国子监的亲身体验证明,张邕不管怎么说都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告诉刘茂,发现这些消息很重要,他会乐于劝导詹士府的同僚们改变这种现状,只要证明有这个必要性。“詹士府并非一个僵化的部衙。”于可远补充说。这句话被证实是战术的错误,却是战略上的正确。“哦?是吗?”他尖锐地质疑,“这个张邕说,他在詹士府时就提出过这个情况并希望上头改变。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官员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规则。这不是僵化的处事办法吗?”他这是退而求其次,伸出脸来让对方打。其实他完全可以将事情推卸在过去的官员身上,但这不免会给自己扣上一层不厚道的帽子,官场要和光同尘,你什么责任都不愿意担,什么事情都要逃避,你的官僚怎么信任你,你的下属你的上司如何与你办事呢?这是信誉问题,并不仅仅是詹士府这个部衙的内部问题。所以于可远装作毫无招架之力,请求主动调查此事。“调查?”刘茂轻蔑地冲他笑。“调查,是的。”他针锋相对地回道。“本官记得,就在不久前你还在裕王府信誓旦旦地说,你们翰林院在与铺张浪费进行无情的斗争,甚至可以成为其他部衙效仿的对象,一番下来,官员数量大幅度缩减,是否有这回事?”于可远点点头。他使出了杀手锏。“你怎么把这些话,跟你们翰林院刚刚招收二十位修撰这件事相提并论呢?”于可远无言以对。刘茂继续问,语气挖苦至极,是不是要提议重新调查此事。这时于可远决定反击了,“刘大人,这个问题,我想都察院的马大人更能回答您?毕竟,马大人经常和吏部打交道,户部难道不是回答这些问题更恰当的人选吗?”马文忠不得不做出回应,并请堂下的公公作证,说一定会将此事传达到吏部那里。那叠倒霉的诗词就从公公手中取走,送到了吏部。很快。吏部左侍郎寻到了于可远,这位也是高拱的亲信。让于可远有些错愕的是,他竟然攻击自己,“大人,”他说,“您把我置于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于可远有些懊恼。本来就是他们吏部实在没有地方安置这些官员,不得不送到翰林院这种没人愿意来的地方,这是他承自己的人情。“大人又把我置于什么境地?朝廷上下,现在左一个节约,右一个节俭,而我却看上去好像是在浪费所有其他人省下来的所有的钱!”这位左侍郎以为于可远发疯了,便解释道:“大人,没有任何别的人省下来过任何钱!这不是心知肚明吗?您到这会儿应该明白这一点。”于可远明白,他也明白,而且他明白于可远明白这一点,包括各部衙的官员们都明白,但所有官员都装作不明白,而百姓们是真不明白。“他们看上去好像是节省了什么似的。”他继续暗示着,然后抱怨道:“您这件事办得太不地道了,为何不能拖延的……”于可远打断了他,“什么拖延?”“把事情弄模糊一点,再模糊一点,您往常都挺善于把问题弄模糊的。就像翰林院官员数量这件事。”虽然这话意在恭维,但听上去并不太像,虽然这话确实是有这层意思的。“大人,您本来有这个能力将事情弄得……嗯,怎么说呢,就是莫名其妙一些。”于可远有些震惊他的直白,不愧是吏部官员,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然后他继续说道,“我这话是赞同,是认可,我可以发誓。您在翰林院,在詹士府做事,把事情弄模糊本来就应该是您的基本功之一。”“那你来告诉我,还能怎么做这件事。”于可远冷冷地回答。他不假思索地给出例子,“拖延决定,回避问题,谎报数据,歪曲事实和掩盖错误。”事实上他完全正确,这就是官员常干的事情。可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掌握的信息太少,根本无法作出更多事。一旦说错,就是更大的陷阱。于可远不理睬这话。“大人,”他开始说,打算从事实角度搪塞过去,“如果这些内幕都是实情……”他立刻打断了,“假设,没错,假设!您本来可以说,比如说,讨论真相的性质。”现在轮到于可远给他解释情况,“这场讨论对真相的性质毫无兴致——他们都是赵大人的属下。”“那您可以说一说安全方面的问题。”他说,这一般都是吏部官员常用的第一道防线。愚蠢透顶!他问他一些腐蚀的铜线怎么能成为安全方面的问题。“这取决于怎么使用它们。”他献计献策。可悲啊,他不可能真的以为于可远这样就能逃脱吧。于可远不打算和他继续在这和稀泥,“所以吏部为什么要往翰林院安排二十名官员?”“这是吏部的基本工作,给没有犯错的官员安排到合适的部衙,这是分内之事。只是原本要安排到通政使司,哪知徐阁老提前打了招呼,往那送了十多名官员,实在塞不进去了。而且……认命文书发得太早了一些,让这些人寻到可乘之机。如果再晚一些,或许就不会这样……”猪队友!于可远只是难以置信地望着他。“只是一丁点儿小错误,”他竟然开始公然挑衅,“任何人都可能犯的那种。”“一丁点儿?”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丁点儿?二十名官员!我们费尽心力才裁减了十二名官员!那你给我举个大错误的例子!”“让他们去找吧。”接着于可远问为什么要给堆满铜线的库房烧炭。“大人,你真想知道?”他问。于可远吓了一跳。这是他第一次这样问自己。“要是不太麻烦的情况下。”他略微谨慎地回答。其实这本该是自己这个詹士府少詹事知道的事情。但显然他不知情,而归功于某些特殊渠道,这位左侍郎大人竟然知道。“某位大人,”他说,“在库房里和其他几位品级稍低的大人做文章。”“做文章不是有书……”于可远立刻止住了呼吸,做文章?做什么样的文章要背着人去无人问津的库房里?这特么分明是在……龙阳?他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他从简而行。“制止他们。”于可远有些生气。这位左侍郎大人摇摇头,发自肺腑地叹了口气,“但自从这一任詹事上任以来就如此了,您总不能向自己的上司提议此事吧?”于可远更是一怔。原来是詹士府詹事……他的顶头上司?所以自己是在给上司抗雷?何况这件事显然是很多朝廷大员都知道的,也都心照不宣地默许此事,他们拿出来也不是真要给詹事大人穿小鞋,就是为了恶心自己!他就更不能去找詹事大人了!于是他接下来想到詹士府订购物资的建议,为何那个张邕提的建议没人接受呢?答案其实显而易见。但左侍郎大人却异常激动地道:“那就是个搅屎棍!一个怪胎,他特别执着于节约,导致自己丢掉了乌纱帽!”“所以为什么不采纳,是谁在吃回扣?”“并没有人吃回扣,大人。”他显然没在说实话。于可远盯着他。“要执行这个建议就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所以呢?”“这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官员。”这显然是在胡说八道。但他却觉得很有道理。“您不反驳我?”“显然,我做不到,你说的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二人达成了相当的默契。“没错。”他竟然开始得意洋洋了。于可远幽幽望着他。他突然就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这些都是你编造的?”“当然。”他大声笑着。“为什么?”他缓缓走到门口。“作为一个例证,”他用那种傲慢至极乃至带着一些不屑和教导的语气说,“来表明如何对付你的敌人,尤其是你的同僚们。”这是在显摆!是在**裸地向于可远证明,他的智慧远比于可远更高明!而接下来的几天,同样的大臣和这位左侍郎见面了。同样是刘茂和马文忠,就张邕的揭发和建议严密地盘问他。而事实证明,在这样一位官场老油条面前,于可远表现得确实更嫩了一些。他有幸旁听了这场讨论,也愈发对这位吏部左侍郎另眼相看。“申时行,申时行,不愧是你啊。”于可远心中默默念着。这人不仅曾在翰林院任过编修掌修国史,数年后便进宫为左庶子,左庶子是皇太子东宫左春坊的长官,职如皇帝的侍中。不过,申时行的具体职掌不是侍从东宫,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掌理翰林院。此后,迁为礼部右侍郎,成为礼部的第二副长官。随后任礼部右侍郎,掌管官吏铨选,职权颇重,列六部的首位。高拱能在吏部有那么多的声音,也是仰仗着申时行。申时行的政治生涯也不仅仅于此,在张居正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回江陵老家服丧时,申时行便被举荐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不久便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后荣列首辅,成为一代贤相。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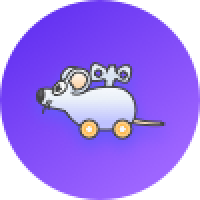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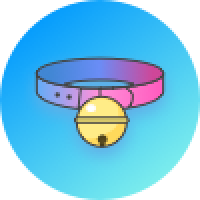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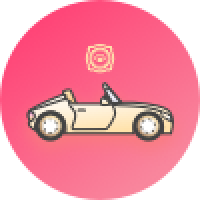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