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投降的兵卒,司提可以下令击杀,因为他是将军,他的目标就是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李余不一样。他是天子,天子要的可不仅仅是一场胜利,更要人心。不杀这些郡军和县兵,只是赢得区区万八千降兵的人心而已,并不算什么,可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乡时,都会宣扬他们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他们会告诉身边的朋友、当地的百姓,燕军对他们无情的杀戮,京师军对他们的宽仁大度。此消彼长之下,有利于朝廷对燕州的收复。李素对这些企图投降的郡军、县兵还算不错,并没有把他们当成降兵处置。不过对于他们成功登上山顶,并一路穿过山顶跑下来,却毫无作为的事,禁不住扼腕叹息。这是多好的机会!如果当时他们能与吴军拼杀起来,哪怕是赤手空拳,这么多的人,也足以搅乱吴军,己方便可趁此机会,一鼓作气的攻上山顶。他叫过来几名郡军校尉,问道:“山顶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众校尉面面相觑,而后纷纷摇头。摇你娘的头!李素气得想骂人,他强压怒火,沉声说道:“你们明明已经登上山顶,怎么可能什么都没看到?”一名校尉怯生生地说道:“将军,当时……当时我等的脑袋都是懵的,也……也没敢四处张望啊!就……就一门心思的往前跑了!”……李素扶额,他环视众人,大声质问道:“你们这么多人,谁都没看清楚山顶的情况?”几名校尉再次相互看看,其中一人小声说道:“山顶……山顶好像有石头屋子!”“不是石头屋子,我看那像是石墙!”“我看更像是城墙!”这些校尉,明明都是刚从山上跑下来的,但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人看到了房子,有人看到了石墙,竟然还有人说看到了城墙!李素恨不得冲上去踹他们几脚。他又叫过来下面的普通兵卒,问他们在山顶看到了什么。他们的说词和几名校尉大同小异,说什么的都有,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见李素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名校尉小心翼翼地说道:“将……将军,您……您也别怪我等没看清楚,当时小人们只想着逃命,根本……根本没心思去打量四周啊!”“是啊!将军!当时我们的脑子都是懵的,而且周围站了好多的吴军,有他们挡着,我们想看清楚也看不到啊!”李素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说道:“下去吧下去吧,都下去休息吧!”众人如释重负,齐齐向李素插手施礼,而后被燕军领着,回营去做休整。其实他们说的话也都是半真半假。跑到山顶上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确实都处于惊慌失措、头脑发懵的状态。但要说什么都没看到,或者说每个人看到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也不现实。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说实话,原因也很简单,没有谁是傻子、呆子,分不清楚好坏。燕军对待他们这些地方军的态度,完全是把他们当成炮灰。像赶羊一样赶着他们上战场去送死,一旦有人调头往回跑,或者驻足不前,立刻便会遭到李烈部下的无情杀戮。可以说燕军根本没把他们当成人看。反倒是山顶的吴军,见到他们放下武器,蜂拥上山后,便未再滥杀一人。还放他们穿过山顶,从南关岭的北侧下山,单凭这一点,他们就打心眼里感激吴军。现在要他们把山顶吴军的情况告知给燕军,人们都打心眼里不愿意。这才有了地方军每个人的说词都不一样的情况。李素令人带走这些地方军后,继续对山顶发起进攻。当天下午,便有大营里的兵卒跑来向李素禀报,说是有好多地方军兵卒都偷偷溜出大营,不知去向。知道这些溜走的地方军都做了逃兵,但李素现在没时间管他们,只能先把这些账记下来,等战事结束后再找他们算总账。被李烈召集过来的地方军数量不少,有三、四万人之多,但仅仅才过了两天,这些地方上的郡军和县兵就逃得七七八八。现在的李烈哪里有心思去理会这些逃兵,他继续令人给各郡各县传书,令地方官府继续征召新兵,输送到南关岭这边。但是这回地方官府接到李烈的‘诏书’后,再未送过来一兵一卒。那些逃回家里的郡军和县兵们,把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四处宣扬。他们当然不会说自己有多胆小,有多怕死,而是添油加醋的说燕军有多残暴,对他们这些地方军有多冷酷无情。他们加入燕军后,燕军根本不把他们这些地方军当人看,燕军对他们任意打骂,甚至一言不合就挥刀砍杀。听完他们的描述,谁还愿意去加入燕军,去为李烈作战?各地的郡府、县府征召不到新兵,而原有的郡军和县兵打死也不再去南关岭,各府衙无奈,只能装聋作哑。南关岭的战事还在持续。双方这回已经不是打到胶着状态,而是打到了疯狂状态。山下的燕军展开了拼命式的持续进攻,而且是日夜不停的攻势。连续三天三夜的猛攻之后,燕军固然伤亡极大,可山顶的京师军也扛不住了。京师军的兵力已由最初的两万人,缩减到不足八千。只这么点人,既要守住南面的山坡,又要守住北面的山坡,还要守住东面的窄道,西面的悬崖峭壁,人手已是捉襟见肘。而且持续不断的激战,让京师军这边的将士完全得不到喘息之机,即便是铁人也受不了。进攻的燕军也明显感受到山顶敌军的抵抗越来越弱,即便连日来出现高额的伤亡,但燕军将士都跟发了疯似的,攻势越来越猛。战斗到第五天,有一支燕军顶着山上滚落的石头,硬是冲上山顶,与京师军展开近身肉搏战。虽然这支燕军很快便被杀退回去,但这却是自打南关岭之战爆发以来,燕军第一次在正面强攻中冲上山顶。就算最终被打退,但也足以振奋人心。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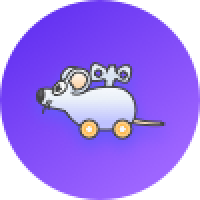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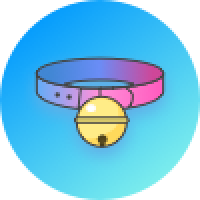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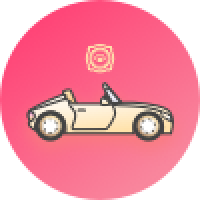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