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碳子一那场再自然不过的迁徙,在我的记忆里,仅仅始于一只诡谲的球体。我正是从我学生口中听说有关那只球的故事的。彼时,我正任教于镇上的重点初中,做学生们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传授知识的过程是我深深热爱的,尤其是面对这群来自乡镇的孩子时—他们淳朴、天真,拥有最原初也最炽烈的求知欲。更难能可贵的是,孩子们总乐意分享镇子里发生的奇闻异事,譬如某家捡到了大块陨石碎片、某家的麦田地里凭空浮现怪圈等。至于孩子们口中的稀奇事,少部分是纯粹的恶作剧,余下的大部分也总能用课本内的科学知识给予解答。挖掘奇妙现象背后的科学本质,在我与孩子们的眼中都是有趣且珍贵的体验。深秋的某个傍晚,放学后,班里的大壮同学忽然跑来办公室找我。他涨红着脸,颤抖的嘴唇中憋出一个秘密:他的老爹刚刚在地里挖到一只谁也搬不起的黑色大煤球。又是一件奇闻异事。我一听便来了兴致,立刻打趣道:“大壮啊,这还真是稀奇!连你也搬不起那块黑色大煤球吗?”“罗老师,瞧你说的!那可是鹅蛋一样大的煤球,我都使出浑身的劲儿啦,就是搬不动。”大壮挥了挥壮硕的臂膀,满脸委屈:“别说是我,就是我大哥和我老爹加起来都搬不动,那只大煤球像是扎根在了地里。”“一家子大力士都搬不起来,是不寻常。”我饶有兴致地追问,“大壮,那只球摸起来质感怎么样,光不光滑?”“让我想想。大煤球摸起来坑坑洼洼的,坚硬、冰冷,可就是一点也不光滑—嘿,我记起来了!那只大煤球表面净是些黑色**,量很大,也很黏稠,粘在手上难受极了。我洗了很久才清理干净呢。”说着,大壮向我展示他白净浑圆的双手。“嗯,那只球真是纹丝不动?”“真的!推拉抬举都没有效果,它可犟了,就是一点儿不动,也砸不开,奇怪得很。我老爹特别担心,说这大煤球不吉利,不许我把它连根挖出来。所以它到现在也只露出了上半截,下半截长什么样还不知道呢,没准真是长在地里的。”没准真是长在地里的……我思索着大壮的话,大壮则瞪着自己白净的双手发愣。不知过了多久,我不经意间瞥向远处。窗外匆匆飞过一列青色的鸟,似乎是赶着要在暮色降临前归巢。队列划过窗边时,我望见它们的翅膀上落满了深秋夕阳的余晖。大壮的眼里也倒映着一片橘红色的光辉,在那里,我望见了无限渴望,无限真诚。这之后的一天里,我始终无法停止对黑色大煤球的思索;放学后独自坐在寂静的办公室里,那只黑球也依旧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心里终究是涌起一阵不安:它真的只是一只煤球吗?如果是,为什么会搬不起来;如果不是,它从哪里来?它的真身全貌又该是怎样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亲眼见见那只诡谲的球了。正这么想时,便听到一阵沉闷而急切的脚步声—大壮同学踏着下沉的夕阳再度闯入我的办公室。只见大壮满手黑乎乎的黏液,眼里尽是焦虑与恐慌。“罗老师,那只黑色的球,长大了!”二亲眼看见那只黑色球体的瞬间,我深深信奉的唯物主义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丝动摇。此刻,我魂牵梦萦的黑球,正纹丝不动地“悬浮”在土壤表层,与沃土止于游丝般的联系;覆盖着黑色流体的球体表面正缓缓膨胀,截至现在大约一只篮球大小。但它又是极安静的,那粗糙的质地和浑厚的黏液,并没有显出一丝侵略性。似乎是为了防止黑球玷污庄稼人的心血,黑球四周的冬小麦都被铲了个精光,大片田野重归寂静和荒芜,远远看去像是中年男人的头顶。此刻,寂静的黑球、荒芜的土地、落日的余晖和余晖下的二人,拼接成一幅奇妙的构图:我与大壮恰似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伫立在地中海,凝视着圣物,心怀世间一切敬畏与虔诚。凝视着黑球,我只感到无限阴森,像是同时被它凝视着一般。橘红色的夕阳漫过深邃表面,鲜艳的短波被彻底吸收,只余下同黏液一致的漆黑。这极致的漆黑里蓄满了球的神秘,蓄满了我的困惑,也蓄满了庄稼人的无尽忧心。这只诡谲的黑球已然超越了我的解释范围。“罗老师,我没说谎吧?”大壮的额头渗出汗滴,一会儿盯着球,一会儿盯着我,“这只大煤球……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不是真的不吉利?”我缄默着。它正在生长,它是生物吗?不一定。疑点在于,克服引力维持悬浮态或是膨胀式生长都需要消耗能量,可它通过何种途径吸收这些能量?抑或是单纯的光学现象?不,这更不可能,因为大壮近距离接触过它,它是实体,它的质量就在那里,不会骗人;也绝不会是恶作剧—究竟要多么高超的技术,才能伪造出这样精巧的骗局?更令人费解的是,假设它是生物,又为什么只扩张半径,而不运动?要知道运动是生命的内在规律,可这只球从始至终只是沿径向扩张,却从不见运动,甚至从未改变自己的中心位置分毫。“大壮,这的确很不寻常。”我试图维持人民教师应有的冷静,“但是不要急,要镇定。你能触摸到它、我能观测到它,就说明它也是再平凡不过的物质,其一切行为必然符合数学、物理定律。既然符合科学,就一定能用科学解释。”“罗老师,可以求求你用科学解释它吗,像以往每一次那样?”大壮浓厚的眉毛紧紧纠结在一起,“我的老爹很担心这是不祥的兆头,我也很害怕。”我可以用科学解释它吗?镇定下来,挣脱直观的惊异与震撼,那也不过是一只悬浮在土壤里的黑色球体。它缓慢膨胀着,然而截至此刻仍是篮球大小,在苍茫的田野中那样微不足道。更不必说,它始终驻足在同一个位置,像是一颗浑圆的、稳定的铆钉;表面的黑色黏液也流淌得很缓慢,看上去安静极了。仔细想来,它身上并没有一处挣脱科学的解释范畴,不过是各种异象的拼接罢了。安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最困惑的地方:它太安静了,漆黑与安静正是涌现未知的源泉。一个未知的生物,既然有能力径向扩张膨胀,为什么不作水平或垂直机械运动呢?广阔的田野也有的是场地供它驰骋,它却为什么只是始终悬浮在原地?初冬的夜幕之下,我看见强风拂过庄稼,在它们的尖端点燃最后一丝光明;更远处,土拨鼠钻进地里,蚂蚁爬入小窝,鸡鸭回笼,雁雀归巢。黑色球体依然安静地悬浮在麦田地里,像是伴着夜幕缓缓入睡—它们都静谧极了。不过是回到自己的归宿,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老师也一时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拍着大壮的肩膀,“不过,老师说不清楚的事物,就请老师的老师来说清楚吧。他们啊,知识更渊博,心思也更缜密,一定会有办法。”第一时间,我便想起老陈。三老陈是第二天大早赶着飞机来清水镇的。“小罗,你认为应该如何研究它呢?”老陈近距离端详过那只黑色球体后,笑着问我。那和蔼而自信的笑容是我在读研期间多次见过的。每当老陈这样笑着向我抛出课题,我就确信,这课题一定有解、有价值。所以我猜测,老陈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不过,我的脑海里依旧乱糟糟的。在那漫漫长夜尽头,黑色球体已和寺院门前铜狮雕像的头颅一般大小。它依旧安静,却愈加散发出压迫感,迫使我们维持长久的缄默。长夜里,大壮父亲坚持认为球与土壤的直接接触是不祥的,这位憨厚的庄稼人一声不吭地劳作了大半夜,清空了麦田一角,留下一只巨大的坑洞以供黑球生长;至于大壮,早已难敌困意,卧倒在不远处的田埂上呼呼大睡;我则不遗余力地整顿着思绪,端坐在黑球面前,直到东方透出一抹晨曦。“应该如何研究黑球?我认为最基本的,是要先采集表面黏液,鉴定其生物成分、分析其化学构成。如若可行,切割球的一部分作为样本,送到实验室进一步解析材质的力学性质、光学性质。但尚不确定这只球是不是生物,这么做可能会惊扰到它。”“说了半天,为什么不把这只怪球整体送到实验室呢?”老陈笑眯眯地问我,“那样不是更好?”顷刻间,我意识到,截至此刻,那只黑球依旧静滞在原地。纵然半径缓慢扩张着,黑球的中心位置似乎从未改变。在我那固执的潜意识里,它好像就应当是静止的。“从我观测开始,它就一直悬浮在那里,纹丝不动。”我答道,“我的学生也正是经由这一异象注意到它的。陈老师,它真的能够被挪动吗?”“不一定。”老陈说,“这也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假定它是一个生物,你说它要什么时候才会维持径向成长,而中心位置静止不动呢?”“吃饱了睡觉的时候?”大壮蹲在不远处的田埂上大喊。“想象这么一种情况,一只小鱼在水底铆足了劲儿向上游,跃出湖面,带起一串水花,”老陈望向大壮,仍是慈爱地笑着,“随后,小鱼在最顶点失去动能,竖直下落。从鱼嘴接触湖水的那一刻起,湖面就留下了一串它的印记。假定鱼是规则的球体,那么以湖水为截面摊开一张白纸,白纸留下的小鱼的印记,随时间变化的情形该是怎样的?”我开始想象老陈所说的情景。起先,鱼嘴接触湖水的那一刻,白纸呈现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点。紧接着,小鱼的身体不断没入水中,截面那个孤零零的点也逐渐扩大为圆。直至小鱼上半身浸入水中,截面圆的半径达到最大。此后截面圆缓缓缩小,最终归于一道线—那是鱼尾的痕迹。截面终将什么也不剩,除了一串证明其存在的涟漪。“我想清楚了!”大壮激动地瞪大眼睛,“黑色的球也是一只穿越湖面的小鱼,我们的田野就是那片湖面。”“小胖,你几乎说对喽。”老陈摸摸掉了漆的老花镜,“那张白纸,可以用来比拟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设若存在某种更高维度的小鱼,当它们穿越我们的世界时,留下的痕迹就将是这只膨胀的怪球,或许也伴随着一串可观测的涟漪。”“陈老师,你是说,高维度生物?”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不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东西……”老陈沉默片刻后回答,“即使谈到所谓四维生物,它们也不过比我们多一个坐标分量。或许古怪反常,但并不可怕。”说到这里,老陈已经收起笑容。他满脸严肃地与我对视:“小罗,你来清水镇支教,你不了解。近两周以来,我们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现了多个这样的黑色球体—学术界管它叫‘黑鱼’,与之相关的研究暂且还是机密。大体上说,黑鱼们有的悬浮在高空,有的浸没于深海,小胖找到的黑鱼,是目前陆地上仅有的一枚。正因如此,对它展开详细研究的希望最大。”“这群黑鱼跑到这里,是想做什么呢,和我们一起玩吗?”大壮忙不迭地追问。这时,我看见老陈眯着眼望向远处的田埂,老花镜的镜片溢满了阳光。正午的暖阳下,土拨鼠隐匿在小麦腰间,蚂蚁不知疲倦地搬运着食粮,鸡鸭扑腾起翅膀。老陈则是一脸享受,他悠悠地开口:“那是迁徙。不过是黑鱼要游回自己的家了,途经我们的世界而已。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四我们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迁徙。这类周期性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我们熟知的候鸟;部分哺乳动物、鱼类,甚至少数无脊椎动物,也都有迁徙行为。正如老陈所说,迁徙,是生命运动的正常规律,是最自然的事情。我深以为然。进一步的,兴许对于所谓“高维度的鱼”也是如此:季节更迭之际,黑色的鱼儿从一片水域游往另一片水域,成群结队,一往无前。它们会在途中时不时跃出水面,为了规避天敌,抑或进行气体交换。而我们的世界恰似那平静的蓝色水面,一切都平凡极了。话虽如此,同是迁徙,雁的迁徙终究是比蝗虫的迁徙来得温和;鲨的迁徙终究是比草鱼的迁徙更加暴烈。所谓黑鱼迁徙,投影到我们的物质世界该会是怎样的规模?是暴烈还是温和?对于这个论题,老陈始终没有正面作答;每当我旁敲侧击地问起,老陈也总会在一阵沉默后摆出那句老生常谈:“迁徙就是迁徙,怎么,你还能拦住它们不成?”拜师老陈门下做了三年学生,我也多少摸清了他的性情。这位屹立于当代物理前沿的老学者,平日授课是出了名的不苟言笑,绝不讲半句废话;可要是私下谈起前沿的专业难题,他却总是挂上和蔼而自信的笑容,三言两语阐明问题核心。如果某个专业问题能使老陈都支支吾吾、思考良久,这个问题势必也是尚不明朗的,甚至是无解的死胡同。于是,他的遮掩勾起了我的忧虑,但这份忧虑终究还是随着时间一点点消弭。老陈向上级汇报情况的当天夜里,研究团队就已火速赶往清水镇。那支身穿蓝色防护服、在农田边缘搭建白色帐篷的研究团队,吸引了不少农户围观。此后,他们封锁起周边农田潜心研究,便再也没有大动静。些微的**过后,我自是回归学校安心授课,班里同学都不知道黑鱼的事,除了大壮。他也是一如既往地老实憨厚,始终将黑鱼视作秘密。唯有大壮的父亲,每至黄昏,都会来到封锁的农田边上,面朝黑鱼所在的位置合拢手掌。偌大的清水镇一直风平浪静,他大概是镇子里唯一担忧着黑鱼的人。正如老陈所预料的那般,清水镇的“黑鱼”,在两周后达到了最大体积—与半张乒乓球台旗鼓相当。此后黑鱼的体积果然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并预计将于两周后彻底归零。这只布满黑色黏液的丑陋球体,其最终归宿只能是平静地消失。老陈是在一个夜里急匆匆赶来见我,并向我分享这些喜讯的。作为研究团队的特聘顾问兼生长模型课题组组长,老陈在这只黑鱼身上提取了大量参数,以建立精确的“膨胀—收缩”数学模型,其拟合结果也堪称绝佳。用以描述黑鱼生长的一切数据,都精准符合数学模型的预测。“多亏你们,黑鱼终于不再是未知的了。”我长舒一口气,给老陈倒上一杯热茶。老陈没有回应我,而是小口抿着热茶。我捕捉到老陈眉间匆匆掠过的一抹不安。“单只黑鱼的生长模型,还有它的物理、化学性质等,确实是摸清楚了。”老陈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缓缓放下热茶,扶稳老花镜:“然而,我们不知道这样乒乓球桌一样大的黑鱼—或者鹅蛋一样小,这都不要紧,体积不重要,数量与位置最重要—世上究竟还会出现多少,它们又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哪里?这是十分严峻的问题,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绝无办法对它们进行观测或是预知。平静的湖面绝不会告诉你水底藏着怎样的游鱼,三维欧式空间不过是四维欧式空间的一个投影,却也正是缺失的那个分量隐匿着一切危险的信息。”几乎是同一时间,我记起老陈说过的“四维生物不过比我们多一个坐标分量,或许古怪反常,但并不可怕”。想来老陈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白黑鱼事件的核心是什么,然而或许是做了最积极的预期,又或许是为了照顾大壮与我的情绪,他始终没有阐明这一点。老陈眼里的我,大约还是个心灵敏感、思维迟钝的乖学生。他再也没有说话,我也缄口不语。我深信探讨专业课题时的沉默,是思维的润滑油;此外的一切沉默,不过都是无尽的煎熬。两杯热茶也沉默着。它们彼此相对,升腾的热气浸润了陈老师的老花镜片,继而缭绕在屋檐下的挂画前。那挂画中央,清水白莲之间游动着两条红鲤鱼,恰似那缥缈的热气,回旋往复,不知疲倦,终无尽头。五黑色鱼群的迁徙悄然改变着世界的形态。起初,黑鱼是伴随一连串重大交通事故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最早的交通事故发生于日本京都内一条繁华的交通干线。那条主干线在十分钟内连续发生超过三十起车辆失控事故,造成重大伤亡。公路一时间填满了金属碎屑、破碎的肢体与暗红的黏液,实在惨不忍睹,日本媒体称之为“史上最漆黑的十分钟”。经详细鉴定,在所有车辆残骸中,都发现了一个精准贯穿车身的圆形空洞,半径不过3.8厘米,却彻底毁坏了车辆的操控系统。不久后,在距事发区域的上游约一百米的道路中央,鉴定团队找到了罪魁祸首:一只渺小的球形“黑鱼”。夜幕下它静静隐匿着形体,是那样无辜地生长、膨胀,也是那样轻描淡写地摧毁了疾驰的钢铁巨兽。紧接着,各类超乎想象的交通事故接踵而至。远在法国,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撞上一只新生的黑鱼,螺旋桨瞬间报废;及时弹射逃生的两名驾驶员也未能幸免于难,失事直升机附近最终只找到了两只千疮百孔的降落伞。近在俄罗斯北方,一只黑鱼冒着狂风暴雪扎根在西伯利亚运输线的铁轨底端,这只不起眼的黑鱼顷刻间掀翻了数万吨的庞然大物,坚韧的合金化作了扭曲的废铁;同是列车,印度南部的另一班就更不走运了:那班可怜的载客列车撞上了竖直飘浮在半空中的黑鱼,列车左侧的乘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它齐刷刷地洞穿了胸口—像是筷子穿过软糯的芝麻汤圆那样,只剩下列车右侧的乘客呆坐在血腥弥漫的车厢中,恍惚出神。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将黑鱼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喜欢讨论黑鱼,因为未知、因为新奇;却也无比忌惮黑鱼,因为指不定哪一天,自己也将成为黑鱼的受害者。世上究竟有多少黑鱼?未知的黑鱼又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迅速成为上至专家、下至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某大学知名学者在接受公众采访时声称,经过私人团队的不懈研究,他们断言全球黑鱼的数量不会超过五千只。这席话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的定心丸,可就在采访播出的次日,地质学家在莫霍界面[1]附近侦测到大量新生黑鱼,黑鱼总量在世界范围一举突破五千只,直逼五位数大关。定心丸短短一天就过了保质期,恐慌再度战胜好奇,混乱与无序正于暗处悄然滋生。戏谑的是,归根结底,一切事故的罪魁祸首竟是这么一场迁徙—一场再自然不过、再平凡不过的迁徙。难道,我们要将罪孽归结于那些无辜的黑鱼身上吗?六“据美联社报道,黑鱼的频繁出现迫使加利福尼亚州彻底陷入交通瘫痪。政府预计实行最高级别交通管制,并禁止一切交通工具出行。”屋外大雪纷飞,一片凛冽。屋内,我正为老陈阅读今日的重大新闻。老陈窝在温暖的火炉边,双手捧着热茶,眯起眼,津津有味地听我念新闻。“除去交通方面,小罗,再念几条听听。”“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最大的核电站正面临多只新生黑鱼的威胁,或将于近日全面关停。”我念下一条。老陈依旧眯着眼,不为所动,我见状就继续念了下去:“一名滑雪运动爱好者被发现在高空意外身亡,其遗体悬挂于空中长达一天之久,后于头盖骨顶部发现弹丸大小的黑鱼;欧洲有关团队声称,莫霍界面发现的大量黑鱼或将引发全球性地质变化。截至昨日,陆上黑鱼总量已达一百万只。其中,中国境内的数量七万有余……”“真是接连突破我的想象力。”老陈缓缓戴上老花镜,缓缓开口:“看那个可怜的人。不过是在滑雪,多健康的运动,可偏偏就在腾跃到半空中时遇到了新生黑鱼,意外身故,谁又能料想到呢?至于死法,更是荒唐—那只黑鱼竟像结实的铆钉一样把人的头骨钉在了蓝天白云之间。讽刺的是,黑鱼没有罪,人类也没有罪—我们与黑鱼,只是不和罢了。”老陈一席话使我恍惚间想起田野间的那枚黑鱼。起初,那枚黑鱼与老实的庄稼人确乎严重不和。可到昨夜为止,它已收缩至一枚鸡蛋大小,看上去人畜无害,兴许已被鹅毛大雪掩埋在田野里了。许多人相信,绝大部分黑鱼应当还是会像它这样出现在荒郊野岭,对人类社会难以构成威胁,只要扛过个别惨案、等待黑鱼全部消失,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再度恢复宁静。老陈的忧虑与感慨无疑是明智的,可我们与黑鱼的冲突,终有竟时。想到这里,我反而释怀了不少。我端起自己的茶杯,与老陈的茶杯相碰:“陈老师,你说过迁徙是最自然的事情。既然已经经历过这一次,就证明历史与未来都会经历无数次。无论是耐心等待还是奋起斗争,人们总会找到与黑鱼和谐相处的办法。”“小罗啊,你果然是只适合教书,不适合搞科研。乐观与妥协起不了任何作用,不和就是不和,差异绝不因主观意志而转移。黑鱼,只会在我们的世界继续兴风作浪,甚至更加猖狂。”茶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老陈随之叹了一口气:“纵使小石子坠入湖面也该掀起层层波纹,更何况是鲜活的鱼?单单是所谓湖面涟漪,那充盈着能量的一圈圈振动,就足够我们脆弱的星球喝一壶了;更不必说黑鱼二次下坠穿越湖面,肯定只会有更多超越想象力的荒诞悲剧发生。当然这都是科学问题,不完全理解也不要紧。但我希望你至少记住,它们是无辜的,人类也是无辜的,一切不过源于一场平凡的迁徙,像是鸡鸭回笼、雁雀归巢那样,自然极了。可我认为这正是最悲哀的地方。”无论我们能否扛过这场危机,老陈说,黑色鱼群至少教会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平静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以至于我们竟然认为平静才是理所应当的—可其实不是。平静是幸运、是偶然,冲突才是常态。当真正“理所应当”的事情发生时,谁又能有抵御的能力呢?七黑鱼终究是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态。有关黑鱼的两大谜团:数量与位置,前者经过无数血与泪的实践,终于告破。在那事故频发的两个月内,黑鱼的数量已从五位数跃升至十二位数,并逐渐维持稳定。这意味着黑鱼的种群密度已然超越人口密度,而人口密度—自然下跌不少,两个月内约有一亿人葬身于与黑鱼相关的各起事故,每一个鲜红的数字背后都藏着一串令人嗟叹的悲剧。另外,有关黑鱼现身位置的民间研究依旧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起先是一位非裔科学家提出了“弹坑理论”,声称统计结果表明黑鱼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两次。这一论调的公布一度引爆“抢地热潮”,不少富豪开始抢购黑鱼出现过的地皮。曾有房地产老板欲图斥巨资购买大壮父亲的农田,却被这位憨厚的庄稼人果断拒绝了,这位大老板在被黑鱼支配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死得可怜。直到那位赚得盆满钵满的非裔科学家,在重金购置的安全区里被新生黑鱼钻透了颈部动脉,抢地热潮才算平息。然而,不久后接踵而至的“涟漪”,于人类社会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第一起涟漪正是在两个月后爆发的。提起涟漪,我脑海中闪烁的第一幕便是滔天巨浪。老陈肯定了我的直觉,但也叹息后果远不止于这样。事实上第一起涟漪并非来自海上,而正是来自空中。三月初的美国,于亚利桑那州上空接连消失的大量黑鱼引发了涟漪效应,原本平静的卷积云团迅速扭曲,在短短半小时内形成三道巨型龙卷风。其中一道横跨科罗拉多大峡谷直抵内华达州,途中顺手掀翻了拉斯维加斯的几家大型赌场,带来纸牌与金币的暴雨。北冰洋海域上空消失的黑鱼则凝聚了大量冷气团,推动寒潮南下,酿成史上最严重的春季低温,北回归线至赤道的所有春季作物几乎无一幸免;多道寒流交错过境日本北海道,携来巨量降雪,将那里变成再无人烟的冰雪世界。紧接着,第二道涟漪以地质灾害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地壳像是被吹过气一样膨胀起来,原本坚硬的结构变得松散,失去了稳定性。发生在巴西南部的板块张裂活动在短短一周内形成了巨型沟壑,东非大裂谷再也不是太空中唯一可以欣赏到的自然景观;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在亚欧板块与非洲板块的碰撞之下终于爆发,熔岩清洗了西西里岛的每一寸沃土,使这里变为血一样的红色,扩散的火山灰几天后遮蔽了英国全境,骄傲的“日不落帝国”第一次迎来了它的日落。为一切悲剧谢幕的正是滔天巨浪。简单地说,那山峦般的巨浪也是绝大多数人生命中所见的最后风景。许多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无法相信,记忆里风和日丽的和谐世界,会在仅仅半年间天翻地覆—这琉璃一般的星球已然布满火焰、洪流或是冰霜,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过往的宁静祥和再也寻不见一丝踪迹。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无法相信—那样自然的一场迁徙,竟然那样轻描淡写地摧毁了平静的日子。就像丘陵里悠悠的巨象踩过虫豸,原野中疾驰的骏马踏遍鲜花。骏马与鲜花谁也没有过错,但终究是本源性的不和导致了最后的悲剧—骏马毕竟踏过了鲜花,一个无心之举凋零了一个世界。“我们又曾使多少个世界陷入凋零呢?”老陈无数次捧起茶杯,望着**漾的茶水苦笑,那是他在最后的时光里最常念叨的一句话。凋零是常态,风调雨顺才是运气使然。这是大壮父亲告诉我的。这位老实的庄稼人在寒潮中失去了全部心血,却也顽强地守护着他的耕地直到生命尽头。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能忘记感恩。最后是大壮,我亲爱的学生大壮。覆灭清水镇的海啸来临以前,他正悠闲地坐在院子门口吃他最喜欢的奶油蛋糕,那一天是他的十五岁生日。见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咧着嘴说:“罗老师,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呢!我梦见自己穿越到了黑鱼生活的世界,总算驯服了它们—它们可喜欢吃面包屑啦。“我的生日愿望就是驯服所有的黑鱼!罗老师,你最好了,可不要告诉别人。”那是一个久违的晴天,阳光真好。大壮的口中塞满了热乎乎的奶油蛋糕,脸上堆满了微笑。最后,他迎着阳光站了起来,一边愉快地大口咀嚼,一边冲着太阳的方向伸了个懒腰,神态从容安详,像是黑鱼从没出现,像是一切都能重来。涛声渐近。这时,逆着阳光匆匆飞过一列青色的鸟,我望见它们的翅膀落满了和煦的光辉。大壮的眼里也倒映着一片和煦的光辉。在他眼里,我再度望见了无限渴望,无限真诚。那场再自然不过的迁徙,在我的记忆里,正终结于这样一个目光。[1] 划分地壳与地幔的界面,是化学物质和晶体结构的突变边界。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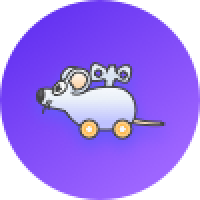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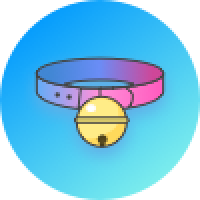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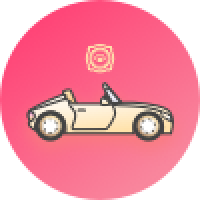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