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觉大活佛自杀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但那时毕竟是连共和国的元勋们都身遭不测,相比之下这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墨班长亲自参与处理了这事件,他是老兵,过去对更觉大活佛有诸多的了解,而今又亲临其境,思前想后总有些耿耿于怀,成天显得忧心忡忡。他和我自然不能谈得更深更多,但是我们各自的心里似乎都是很明白的。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们便接到上级通知,正式离开三村乡回到连队。第一次雪山千里野营大拉练正是那一年的冬天,遵照**“11.24”指示,全军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千里野营拉练。我们藏七连是全团野训部队的先头连。按照上级确定的行军路线,我们从中旬营地出发,途经川滇交界处的重镇奔子栏,继而翻越海拔4200多米的白马雪山抵达滇藏交界的高原山城德钦县而后入羊拉、掠云岭,挥师澜沧江河谷经维西再返回中甸,行程1500华里。这样一条行军路线充分体现了团首长要在艰苦环境中摔打部队的决心。奔子栏是我们千里野营的第一站,这里濒临沧江,位于白马雪山东麓,历来是滇、川、藏三省商贾云集,物资集散转运的繁盛之地。那一夜,我们宿营在奔子栏公社的大院里,就着忽明忽暗的酥油灯,用头发丝穿进脚底板上因行军打起的血泡里,为第二天更加艰苦的行军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夜下了一宿的大雪,我们睡在单薄的被窝里亦感到出奇的暖和。不知不觉天明了,急促的口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匆匆起床,连长简短地做了当天的行军动员,并要求全连人员在半小时内洗漱、吃饭完毕,整装出发。这一天是翻越白马雪山的第一天,行程45公里,宿营地在雪山大拐弯处的3318号道坂。白马雪山是自治州首府通往德钦山城的必经之地和天然屏障,海拔4200米。经过一夜的大雪,整座雪山笼罩在一片白色的雾霭苍茫之中。细如羊肠,逶迤盘折的雪山公路已被大雪遮盖得几乎没了踪影,电话线杆子几乎整个被埋在深深的积雪里。连队的先头班带着铁镐和铁锹在前面开道,我们野训的队伍紧随其后。电影《林海雪原)里看到的一幕,不曾想我们如今也亲临其境了。雪路被我们行军的队伍踏出了一条雪水和冰渣凝结成的通道,我们越往前行,呼吸越觉得紧促,整个肺管和鼻腔里散发出一阵浓烈的腥味。我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雪山高原的行军艰辛。虽然走得很累很苦,却没有一个人掉队,在翻越一道陡峭的雪坡时,马连长还猛然故意地背起了培楚指导员急速前进,显然这是他为了激励全连同志的一个很具有戏剧色彩的行动。这无声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连官兵,身体弱的同志很快地被身体强壮的同志帮助着尽力往前急行。一路上连队的宣传小组发挥了作用,他们从前跑到后打着小木板,数着“同志们,加油走!前面就是宿营地”,“同志们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鼓动词,令大家倍受鼓舞,一下子情绪高涨,加快了行军的速度。有趣的是每到下坡时,大家便不顾一切地纵身在厚厚的积雪中顺着坡势往下冲,大家戏称这是坐上了雪地滑翔机。就这样我们在雪地里整整走了10多个小时,总算到达了当天行军的宿营地3318号道坂。先头打前站的同志已和道坂的工人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宿,烧起了大火塘。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世界上竟有如此的温暖之所。那天的晚餐也是特别的香,每人几大碗热透了的酥油茶就着几大个从火塘里烧烤和从大茶壶煨煮出来的洋芋下肚,似乎把这一天的苦和累都给驱赶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一夜的觉睡得特别香甜,第二天差些误了起床时间。想一想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行军二万五千里的情景,我们这几十公里又算得了什么呢?第三天继续雪地行军,行程只有30公里就抵达德钦县城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走起路来感到特别的轻松,似乎还在意犹未尽中,就到达了目的地。县城里的政府机关和市民倾城出动敲锣打鼓迎接我们进城,仿佛欢迎当年解放德钦城的部队一样。我们在德钦城里休息了一天,待野训拉练的大部队到达后的第二天,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当我们行军进入羊拉乡的时候,驻地的乡民用他们最高的礼遇接待我们,他们从当地喇嘛寺请来了住持,举着幡幛,念着古老的佛经。同时还从家里拿出了成筐成筐风干的鸡肉送到连队宿营的地方。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风干存放的鸡肉,晚餐时全连的主菜就是这风干的鸡肉和着酥油一起炖煮出来的,我们戏称它为“酥油鸡”。我们狼吞虎咽地品尝着这别有风味的佳肴,真的是美极了。在羊拉乡驻训时,有一次,我们派出的围猎小分队,竟然一次就捕获了一家三头野牛。当然少不了又是全连连续几顿的美餐。从羊拉乡出发到毗邻维西县的燕门区的这一段路程是极其难走的。一方面部队还要翻越一座与西藏毗邻的海拔近5000米的哈巴雪山,一方面还要下到海拔仅有几十公尺的炎热的沧江河谷,如此垂直型气候条件下的行军无疑对部队是一次高强度、高耐力、高意志的考验。为了减轻行军中的负重,我们只好把刚刚捕获到的三头野牛,除留少量煮吃外,其余全部无偿奉送给了途中返回的马帮。他们自然很高兴,嘴里不停地说着“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峡谷回声70年代中期我在怒江边防部队工作。可以说这里也是驮负我人生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驿站。怒江两岸曾经留下我的许多足迹,我在那里度过我人生中七年青春岁月。那是一个政治上风云突变,生活上极其艰苦的年代。号称世界第二大峡谷的怒江沟十分的贫穷。怒江两岸壁立千仞,山石嶙峋。除了河谷地带有少量水田和耕地外,山顶上都是贫瘠的鸡窝式的山坡地,只能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一些玉米和洋芋。由于交通闭塞,除了必须统一配发的军用物资外,部队所需要的其他物资,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特别是农副产品。那时部队机关所在地的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六库也还只是一个农村小乡镇。我们是刚从美丽的丽江古城调防来到这里的部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这里地处怒江中游,海拔很低,气候十分炎热。机关开始建在怒江东岸靠近怒江吊桥一带,一块较为开阔的甘蔗地里。后来又搬迁到了六库的后山上。几千部队都驻守在怒江上游数百公里的边防线上。分散的部队形成大小近百个点。全国闻名的泸水县片马风雪丫口和独龙族居住的贡山县独龙江还分别驻守着我们的一个前哨排和一个边防连队。它们曾是闻名全军的独龙江边防八连和风雪丫口排。解放军报曾多次在头版头条宣传报道过他们的事迹。风雪丫口位于高黎贡山山脊,海拔3151米,是个树不长、草不生,终年阴雨绵绵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片马的日军曾经这里到达怒江西岸,企图过江攻占保山的瓦窑,捏断滇缅公路。但是遭到了怒江东岸我抗日军民的奋力抵抗,日军终未渡过怒江。片马风雪丫口一直是怒江边防上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点。因常年风雪,气候十分恶劣。每到冬季都会大雪封山。各级都十分关心哨所的建设。1964年春节前的大年三十,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还从北京亲自打电话到哨所向官兵们问候,祝福节日。几十年来,这段佳话一代接一代,一直在风雪丫口排流传,不断地激励着他们戍边卫国的斗志。那时到风雪丫口和独龙江都不通公路。特别是要进人独龙江全得翻山越岭,爬雪山、过深涧,穿越原始森林,徒步行走几天几夜,路途十分艰难。我1978年夏天曾经徒步进人被人们称为人间秘境的独龙江,在那里我亲身感受了独龙江那鲜为人知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热情好客,勤劳朴实的独龙族群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未去独龙江前,就听说过独龙族妇女面的故事。这次来到独龙江,对她们为什么面才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在历史上独龙族就是一个弱小的民族,独龙族妇女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贞操和生命就采取了面这种手段。这也是弱小民族中弱小女子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说起这种面,着实令人惊心。也就是要把脸上的皮肉当作大图章的表层,用钻刀按着臆想的图案刻出纹路来。而更多的妇女是自己给自己刻的。她们先想好一个自己中意的图案,对着水塘,用炭头把这个图案淡淡地画到脸上,尔后取一枚骨针,在火上灸烤一阵,把针尖烤烫,就开始照着炭画的线条一路戳将下去,戳得满脸鲜血淋淋,在血迹还未干的时候,用一种叫“火神树”的叶汁涂到脸上,这种叶汁的墨绿色就永久地固定在创口之内了。原来,面图案大都是这个氏族所崇拜的图腾。她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要得到男人们的爱慕和尊崇。这种看似十分痛苦甚至近乎残酷的面方式一直在独龙族妇女中祖祖辈辈沿袭下来。我的一位好朋友,军旅作家尹瑞伟曾和我一起在怒江边防部队工作。他曾多次到独龙江采访,并专门写作了一部反映独龙族生活的中篇小说《面女人》。这部小说由天津百花艺出版社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我在独龙江还亲身体会了长期战斗在艰苦环境中的八连官兵的生活。也深深为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为此,我还专门撰写了《一根拔河绳的故事》,宣传他们热爱边疆、安心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的先进事迹。稿件刊登在了《体育报)的专版上。这也是我们部队当时第一篇上中央级大报的稿件。我一直把这篇稿件珍藏在身边。我也一直把它作为为部队官兵服务的一个样品。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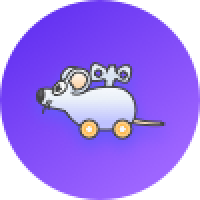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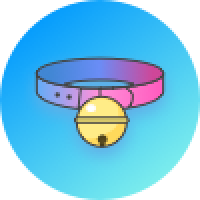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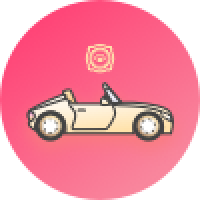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