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过德姆拉大雪山应该说是很顺利的,没有遭遇什么突来的风险。全政委讲,其实这个季节同样也是德姆拉风云突变的季节。翻越过德姆拉大雪山,一路南下,我们开始看见了绿色的山,绿色的森林,呼吸也变得轻快了。我们的车沿着仍然崎岖狭窄的山道向边境县城——察隅驶去。察隅是与印度和缅甸接壤的一个边境小城。位于西藏东南部,行政区划归属林芝。县城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全县人口不到3万人。生在两山夹峙的缝隙里。但海拔很低,手相连。怒江境内的独龙江就发源于察隅境内的恩梅开江。我们军区的一支边防部队也就驻守在这里。县城不大,部队机关几近占去了三分之一多的面积。部队机关环境不错,西藏部队氧气充足,气候宜人。与我曾经工作过的云南怒江携长期存在的“三难”问题在这里还不是十分突出。得天独厚的是县城边的山上有温泉,团里把温泉水接进了团部。于是成了西藏军区名副其实的温泉第一部队。察隅地方虽然小,却是边关重隘。1962年这里的边境曾是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的重要战场。第二阶段作战中,在东段最著名的两大战役之一——瓦弄战役就发生在这里。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对印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烯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由于历经作战又地处边境,这个以藏族、门巴、珞巴族和僵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民、军政关系有着优良的传统。县委书记和县长来看望我,讲得最多的是军队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书记是从广东援藏的干部,思想比较活跃,县长是当地民族干部,人熟、地熟、情况熟。可以说是优势互补的一对搭档。察隅是国家授予的全国双拥模范县,我和团长、政委商量一定要借助这个东风把察隅县的双拥工作做得更有声色,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维护边防、社会的稳定。如今在察隅县城高高耸立的双拥纪念碑就是那次军地达成共识的成果。在察隅,我们的乍队多次与上学的孩子们相遇,见到车子开过来,孩子们都会整齐地站在路边敬礼。随行的当地干部告诉我们,解放军当年夺回来了这片土地,当地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十分感谢解放军,所以每当看到解放军的车队和战士都要敬礼,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说起守卫国土,我们会认为这是军队的事情。但是在察隅,在边境确是每个国民的责任。竹瓦根镇的杨书记是一个敦厚的彝族干部,他1994年大学毕业申请来到西藏察隅,一干就是十余年。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妻子也动员到了察隅。他对我说边境地区人人“守土有责”,这每一寸土地都要实实在在地靠我们的人民占领着。他们镇的边境上,有13户边民,有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也不能搬家,这就是守土之责。在察隅我们实际控制的1.9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26000多名各民族人民,其实他们也是在守卫着我们的国土,他们在为共和国默默的奉献着,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只要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在雪山、丛林上飘扬,这片国土就永远属于中国。察隅有几百公里的边防线,出人的口子也不少,边防巡逻执勤任务很繁重。部队多数驻守在离团部200多公里外的边防线上。最远最艰苦的是至今还不通公路的日东前哨排,担负着中缅边境一线的巡逻守卫任务。而比它更艰苦的可以说就是边防团骡马运输队和他大名鼎鼎的队长尹祥美了。我到西藏军区后就听说了尹祥美的名字。政治部领导和宣传处处长给我汇报过军区正在组织宣传尹祥美事迹的事。军区也明确我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这次到昌都也是重任在肩。我一路上抽时间阅读过尹祥美的一些材料。事迹很感人,就是还缺乏思想的深度和空间。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第二性的感觉。昌都军分区对这件事很重视,党委专题开会做了研究,我到昌都后他们又给我做了具体汇报。成都军区也派出了组织部副部长带队的报社、创作室、新闻处一干人马去了日东前哨排采访、调查。在邦达兵站小息时,我就和他们回撤的人员不期而遇。从他们极为疲惫的面容上,可以看得出他们这次的日东之行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李副部长整个面部都浮肿得变了形,他自诩地说:都快变成猪八戒了,作家施放对我说,他的这条小命都险些丢在去日东的路上了。他们简要的给我谈到了和尹祥美一起进日东的情况。结论是太艰苦,太危险,太难以想象了。不要说像尹祥美那样14年坚持走下去,就是走一次也感到艰险异常,刻骨铭心。在骡马运输队我见到了队长尹祥美。他刚带骡马队随成都军区工作组去日东前哨排送物资回来。见我的时候似乎还没喘过气来。他是我的老乡,重庆大足人。中等个,脸色是明显的“高原红”。看上去是一个性格率直又极老实笃厚的人,不怎么会说话,还有些紧张。他很平淡地给我讲起他们骡马运输队的事,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很普通,也是应该做的。从他的谈话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貌不惊人的骡马队长思想深处,竟然有那么多看似平凡、朴素,而又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东西。他多么像一颗并不起眼的磁石,没有耀眼的光芒,却有异乎寻常的磁力。我在想,在他们看来那些平常的事,不仅已经感动了我,也一定能感动大家,感动中国。那一天,我还意外地发现一幅挂在尹祥美宿舍墙壁上的书法。那是他自己饱蘸浓墨,亲笔书写的一个“马”字。我在想,这个“马”不就是他和他所带领的那支高原骡马运输队的象征吗?在尹祥美的心中,骡马运输队不仅是他已经走过的14年,而是他一生追求的事业。18年在边关驻守,14年与骡马为伴,为“高原孤岛”官兵源源不断地送去给养物资,被官兵们亲切地誉为“雪山牦牛”。爬雪山,蹚冰河,穿越沼泽地,14年马夫生涯,尹祥美等于走了两次“长征路”,将400多吨物资及时足额地送到边防哨所。从骡马队到高山哨所,近的有140公里,远的有320公里,途中亘着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20多条奔腾咆哮的冰河、20多公里危机四伏的沼泽地和一大片阴沉而恐怖的原始森林。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在悬崖峭壁间蜿顿盘旋……这就是尹祥美14年来年年要走10多次的骡马道!这就是维系哨所官兵生命安危的雪域卨原补给线!1987年7月,当兵5年的尹祥美从成都军区后勤士官训练大队学成归来。接到命令,他就搭拖拉机到了骡马队,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马背生涯。这支全军目前唯一在编的建制畜力运输部队,主要负责两个不通公路的哨所战备、生活物资前运。日东哨所一年有8个月大雪封山,只有6、7、8这三个月才能把物资送上去,可这3个月也正是日东的雨季,尹祥美和运输队几乎三天两头遭雨淋,多时一天要淋六七次,全身没个干爽地方。最令他们头痛的是,经常会遇到滑坡、洪水、泥石流,一路上,尹祥美和战士们不知要开多少条路,架多少座桥。有时候,前面好不容易开出一条羊肠小道,还没等后面的人马过去,滑坡和泥石流又把路给冲毁了,只得重新修。午夜,被狂风暴雨惊醒是常有的事,有时大风卷走帐篷、被子,他们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冻得上牙打下牙,只好几个人抱在一起苦挨到天亮。大雪拉山口有一段30多公里的必经之地,大部分地段常年受雨水冲刷,其间有一段路面只有几十厘米宽,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别说走过去,就是看一眼都叫人腿肚子打战。尹祥美把这个地方称作“鬼门关”。每次到这里,他和战士们只能把骡马驮着的物资全部卸下来,将骡马一匹匹小心翼翼地牵过去,然后他们把物资一点一点地背过去,再给骡马驮上继续赶路。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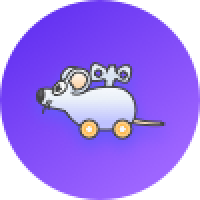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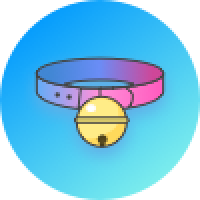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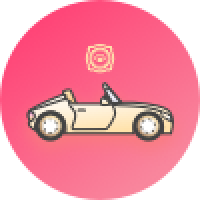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