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座已经直辖,有着3000多年古巴渝化的城市,正在新的起点上扬帆起航,历史又展开辉煌灿烂的长卷:长江是她的魂魄,大海是她的方向。如今我这个远离故乡的游子亦和这座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着新旧交替的母亲城共同吟唱着那首气势磅礴的《长江之歌》。是长江孕育了永恒的重庆,同样是长江孕育了永恒的我们。我们是长江永恒的儿女。北京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从我的故乡——山城重庆走出去认识的第一座城市,竟然是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那是正经历着历史风雨的40年前的北京。秋天的北京城正是枫叶红了的节候。我们依催在秋高气爽的京城怀抱里,初恋式地享受着这座古老都城所呈现给我们的高贵、大气、繁华和尊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长安街如此笔直宽广的大道,见到了**如此金碧辉煌的城楼和宽阔平坦的广场,见到了气势恢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故宫、长城所展示的如此内涵丰富的中华化。见到了王府井、大栅栏繁华热闹的街市、京味十足的四合院和同样京味十足的北京烤鸭。第一次认的北京,给我留下了王者气十足的不同寻常的印象。第二次走进北京,那已是刚从历史风雨中走出来的26年前的北京。我是到了玉泉路上的一所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深造。于是我有了和正把握着新的历史机遇的北京城长达两年时间的亲密接触。我第一次乘上地铁,第二次来到15年前到过的**广场。我随着祭奠的人流第二次走进了新建不久的**主席纪念堂。我曾在这里久久地伫立沉思:伟人也是常人。在痛苦寻觅中找回真理的中国人,又终于回到了真理的轨道。我真的是和北京有缘,以后的时间我又多次来到北京,仰慕北京城那日益繁华兴旺的都市风光和依旧灿烂如新的历史化。我一次又一次地和我所到过的城市做比较:北京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它少了上海那样总是有几许阴柔的小资情调,多了京都总是阳刚十足的大气豪放。它谈古论今:历史悠久,大道朝天,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真可谓皇城内外,王者气十足,非其他任何城市所能企及。是名副其实的华夏之都。如今我女儿、女婿亦定居北京。北京更是与我有了不解之缘。上海我生长的城市与我要说到的这座城市有着“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别一样的情分。我曾两次到过这座名满中外的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是在那个正经历历史风雨的年代,我第一次来到黄埔江畔,来到了40年前的大上海。我下榻在一处叫远东饭店的住所。我总记得每天所能享受到的非常资产阶级化的服务:早晨,饭店的服务员,就会按时轻轻扣动你房间的门铃,并把一杯温热的牛奶和一盘带刀叉的西式糕点和水果送到你的床前,并微笑着向你说出第一声吴侬软语,表达一天中最早的问候。那时毕竟还非常年轻的我,竟感到了一阵阵地诚惶诚恐。这恐怕就是我最早感受到的十里洋场上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小资情调。后来,我开始在那条著名的南京路游迤。我亲眼所及这座与黄埔江共同长大的大都市的历史。洋街、洋房、洋名、洋号……还有黄埔江畔那对对缠绵柔情中的红男绿女。更是把我的思绪带到了西方。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的人们对封闭的封建主义的鄙夷,对开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我第二次来到上海,已是相隔近40年的2005年的夏天。我又一次感到了高温暑热中的上海,那依旧是小资情调浓烈的生活。当然也感受到了这里也正在发生着的更加现代化的变化。我又一次去了南京路,如今这里更是繁华热闹,不仅洋街、洋房、洋名、洋号依旧,更是生长出一幢幢超乎寻常的中外合璧式的摩天大厦,洋人也是满街跑。我在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阳光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正是在这样走出深宅,更加大胆地引领着这座充满小资情调的城市走向更加地时尚和辉煌。我依然看见了黄埔江畔那成双成对,更加柔情缠绵的帅男靓女,那倾洒在黄埔江江面上如诗如画的万家灯光。我第一次到了浦东,40年前这里还是远离资产阶级生活的乡下。如今却成为引领新生活的上海人的骄傲。我们登上仰慕已久的“东方明珠”,我们在标有最高米数的塔顶上俯瞰大上海,更是由衷地感到虽仅只100多年历史的这座城市,却是在迈过了多少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沧桑,才终于走到了今天的辉煌。于是我想到北京的王者之气,那是首都的禀赋。上海的小资情调却是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方向。上海不同于北京。北京不同于上海。北京和上海始终是引领中国城市时髦和时尚发展,不断走向世界,走向辉煌的最有资格的榜样。天津天津和我的家乡重庆是处在完全不同地域中的两座中央直辖的城市。现在都在各自打造着北部和西部的经济中心。天津亦是我在北京学习时,多次去过的一座城市。我接触天津,是从天津人那韵味十足的天津话开始的。我开始觉得这天津话真的是有些好玩、好笑。怎么离北京如此近的一座城市,却没有了京腔,反倒是怪有意思的津味儿。后来才知道,这“天津卫”可不能小觑,它的开埠和开放之风却是领先于北京。自然这听起来虽然有点怪怪的,不像北京话那样动听的天津话,就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原汁原味儿。就像天津著名的狗不理包子和大麻花,绝不会去沾上北京豆汁儿和烤鸭味儿。我曾和天津的朋友谈起北京,他们那平淡的表情里,没有丝毫对这座皇城崇拜的眼神。天津人从来把北京看作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我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感觉这座城市太过平面,没有太多令人惊羡的格调。也许是天津人不好张扬的性格,给这座城市涂染上一副处世不惊,毫无波澜起伏的颜色。我只记得这座城市里曾有过一位叫做张伯龄的老人,70年前到我的家乡创办了一所著名的学校——重庆南开中学。我对这位老人一直深藏着一份崇敬和景仰之情。因为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我是曾经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一名青年学生。在天津,我还无数次地听到过一个耳熟能详的,令天津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说项:北京人结婚,竟会倾家出动到天津来举办婚礼,宴请宾客。北京人渴海鲜,竟会走出京城到天津来,坐在勃海边的海鲜店里海吃山喝,不分白夜。原因是天津城的物价比北京城的物价低。原因是天津临海,而北京则无此区位优势。至今天津和北京两座华北平原上最大的城市都还保持着一种极其矜持和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象则有如重庆人和成都人,两地人亦是异乎寻常地少有谈婚。大连大连这座城市我曾去过两次。两次大连之行,都出于“疗养”这样同一个原因。第一次去大连是随军区疗养团,住在海边一处风景宜人的军人疗养院里。因为是夏天,第一感觉是这里海风习习,少有了夏日的酷热。第二感觉是这里凌晨三四点钟,东方就露出了鱼肚白。第三感觉是这里的海浴,使我们这些不临海的南方人,感到了在大海中遨游的酣畅淋漓。第四感觉是疗养院里开设的第一堂疗养课,竟是心理问卷咨询。疗养院的生活使我们这些长居高原缺氧环境的人呼吸到了负离子丰富的空气。也同时有了低海拔醉氧的反应。那一次的大连之行,由于是集体行动,行也匆匆,未及留下太深印象。只感觉大连的都市情调有些轻音乐似的悦人、悠然。她不是一座恢弘大气的城市,却是一座动情的城市。湿漉漉的空气中,依然飘动着海风带来的淡淡的渔村味儿。第二次去大连亦是去疗养。不过不再是跟团,而是完全个人疗养性质。这次在一位友人的陪同下去了大连很多有名的地方。我终于第一次到了心仪已久的棒槌岛。那兀立海浪中的小岛有着许多美丽的故事和传说,给人以远离时空地无限遐想。我第二次到了旅顺港,再一次走进了那座令人感到恐怖幽深的监狱,这里记录下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累累暴行,我在这里的留言册上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吃人的野兽们终将被英雄的猎手斩尽杀绝!”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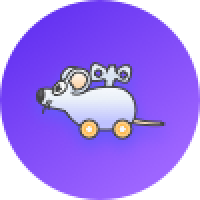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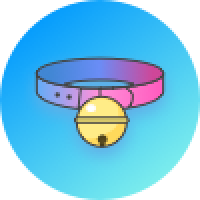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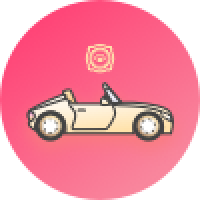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