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脑海里呈现的是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兵。他姓姚。他1980年入伍。当新兵时就被分配给我当了警卫员。那时我还很年轻,而已经是一个野战团的政冶处主任了。边境自卫还击战第一仗打完后一年多,1980年10月15日我所在的团又接受了收复失地的边境作战任务。经过激战,我们夺回了失地。主攻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主峰。我受命带着宣传股长和一名干事荷枪实弹地穿越过原始丛林,翻山越岭向主峰进发。我们要带去前线指挥所和团里的慰问和指示。小姚自然是紧随其后。他身上背着两支冲锋枪,胸前和身边的弹袋里装满了子弹和手榴弹,这是因为刚刚结束战斗,怕在原始森林中遭遇敌方特工和残敌的偷袭。当我攀爬一座山岩时,不曾想手中抓紧的藤蔓正在慢慢脱离山岩,我不经意地听到身后的小姚喊首长!”我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跌落到了小姚的怀抱里,他死劲地抱着我靠在了悬岩边一棵已被炮火打焦了的大树上。我回过头看了一下那大树下边就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谷。小姚抱着我,也惊出了一身大汗。站在另一边的宣传股长赶快伸出手来把我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这样相互帮助着攀援到了主峰。主峰上的战士们见着我们便拥上来和我们抱在一起,一个个激动得泪流满面。我们在主峰阵地上正组织战士们修复表面工事,挖坑道和猫耳洞以防敌炮火反击。前指又发电指示部队马上组织回撤,阵地交给边防部队驻守。战后,团里组织了评功评奖。由于我的工作疏忽,竟然忘记了给救了我一命的身边的警卫员小姚报功请功,甚至连嘉奖都没有给一个。事后,我曾问过小姚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没有啥子想法,保护首长安全是我的职责,是我应该做的!后来小姚服役期满退伍回到了楚雄大姚农村,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踏实肯干,现在已经是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多年过去了,小姚那张年轻的娃娃脸时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时是多么年轻,甚至可以说还是一个孩子,然而他对一个士兵责任的理解,却是于平凡中显得那样崇高,那样忠心赤胆。我时常也在寻味着崇高这些字眼,其实在这些看似多么平常普通的士兵身上,不就无时不刻地用自己的行动在对它做出最好的诠释。说起这件事,说起这个我至今都还不知道他姓名,然而对我却有生死之恩的人,还是应该让时间倒回到n年以前。那时我作为下放锻炼改造的军医大学学员被安排到昆明军区的一个测绘大队作随队军医。这个大队正执行地处澜沧江边的云南维西县巴迪地区的大地测绘任务。测绘最高点就在澜沧江西岸相对海拔约6000多米的高山顶上。我们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山顶,并安营扎寨下来。这里空气稀簿,含氧量极低。真的是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山都是一片片风化石。真没想到才过了两天,我这个本来是保障测绘队员身体健康的军医,自己反倒先生起病,发起高烧来。我自己以为是感冒就吃了些阿斯匹林一类的降温药。但病情一直未减,全身仍是感到一阵发冷,一阵高热。看到我这样,测绘队领导就下了命令,要我下山去公社医院治疗。根据我自己的诊断,我想我一定是在山下时遭了蚊虫叮咬,上山后发了疟疾。在山上携带的药品中就没有治这种病的药。我只得乖乖服从到山下治疗,如果不这样,不仅会延误了治疗,有生命危险不说,也会给测绘队工作带来拖累。可我自己一个人已经虚弱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步行下山。队领导想到了配属我们运粮背水的民工。当他们向这七八个民工征求意见时,多数人都面露难色。你想,要把一个百多斤重的人从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顶上一直背到江边,该要走多少£路,付出多少体力,担当多少风险。正在大家犹豫不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民工自告奋勇地说:“我去!保证在今天之内把吴军医背下山。”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位身体并不十分强壮,显得有些精瘦,眼睛有些眯眯的中等个子的中年男人。一路上我才知道他是傈僳族,家就在江边的一个傈僳族寨子里。他在背负我的过程中,我看到他吃力的样子,我有好多次要求停下来让他搀扶着我步行,可他始终没有答应我,只是在途中歇息一会儿,又继续背着我,吃力地前进。我扶在他的背上,感到了他满身的热汗和粗粗地喘气。最终我们来到了江边,来到了寨子里他的家。那时天色已经很晚,他建议我今晚就住在他家里。他吩咐家人很快给我们打了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并在火塘边爆出了一大堆包谷花。我就按照他们傈僳族的习惯喝着茶,吃着包谷花。后来他又给我准备好了睡觉用的蚊帐和被褥。他告诉我这套被褥是他在部队当兵时用的,退伍回来后一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地存放在箱子里,从未再用过。那一晚我躺在这还留有肥皂余香味儿的被窝里想了很多很多,我不禁默默地为这个于我有救命之恩的似曾相识又非曾相识的老兵为我所做的一切深深感动,我幂幂中只觉得上天有眼,让我在生命中相识相知了这样一位情深义重的傈僳族大哥。我的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亦很快痊愈。后来,我们测绘工作结束,临离开前我去向他道别,并把我的一双新军用皮鞋和50元钱送给他以致感谢!可他却执意不愿收下。最终他也只是同意收下那双皮鞋做个友谊的纪念,而钱却分不要。他说我们都是军队培养的兵,不能这样做。时间亦同样过去了30余年,可这件事却始终难以忘怀。那位曾经于我有救命之恩的,竟然由于自己的粗心连姓名也没来得及记下的傈僳族大哥,我们的老兵不知现在生活过得怎样?我是多么地想念他们!这一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叫小扎史,傈僳族。云南德钦县霞若区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藏七连九班班长。我是下放到他班里锻炼改造的学员战士。他对我一直很关心。在那个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了一种贬意。社会上把它排到了“臭老九”的行列。可他对我从不另眼相看,于一视同仁中还给了我不少照顾。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读过几天书,化很低,要我抽时间帮他补化。他告诉我,他体力好,军事技术也很好,这方面他也可以帮帮我。就这样我们结成了帮学对子,那时叫做一帮一,一对红。有一天,他约我来到连队院子外面的一个小山坡上,和我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事,其中问到了我个人和家里的很多情况。他对我说,像你这样从大城市,大学校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在这样艰苦地区的基层连队安下心来锻炼自己,真的是很不容易。根据你现在的表现,我觉得你应该提出入党申请。这也是我们党小组的意思。那时对于人党我一直觉得是个很崇高的目标,也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条件和资格。所以也就不敢轻易动笔去写人党申请。真的是没想到班长给我谈的是这么一个严肃的政治生命问题。从那以后,我郑重地向连队党支部写出了入党申请,后来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组织考察和政治审査,才终于如愿以偿地加人了党组织,成了一名光荣的**员。于是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走人我政治生命的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藏七连三排九班班长小扎史,我的傈僳族好大哥。后来,我听说他复役期满后退伍回到了霞若家乡。前些年我还通过在迪庆军分区任政委的老战友和家灼打听过他的消息,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真正是茫茫人海,物是人非了吗?我不禁唏嘘!我在我们那个年代,算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班子”。在部队而言所谓“班子”就是对团以上党委各级领导机构的一种特定的称谓。因为进人了“班子”,当然就有了与班子成员的相识、相知、相处。我最先进人的是一个野战团的“班子”。班子中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4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都差不多已是四十七八岁五十岁左右的年龄。比我要大了近二十岁。团里班子比较大。除了团长、政委,还有三位副团长、三位副政委。我是政治处主任,上面就垂直领导关系而言有四位政工,四位军事,共八位领导。横向的关系当然还有参谋长、后勤部长。班子虽然大,但那时的关系却不像现在这样复杂。那时大家都很坦诚,亦很真诚。有啥说啥,想啥说啥,哪怕有时会上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一下来照样一块嘻嘻哈哈,一股子战友甜蜜劲。我尤其记得那时党委的民主生活会,那真是有点火药味。班子成员,无论领导,被领导一到会上都是直呼其名,直点其题,一点也不遮掩马虎。表扬恭维者少,批评点问题多,没有抽象原则,只谈具体事实。有人说这叫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洗脸洗澡大扫除,确是名副其实。多少年后,特别是现在,我总在想那时的风气有多正,那时的风气如果能带到现在该有多好!于今班子的成员,除了有两位同志最终晋升到军职领导岗位外,其余的几位都早早在团职岗位上离休退休赋闲。前段时间我到一处干休所见到这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虽已是白发皓首,但讲起当年一起相识、相知、相处的那些往事无不又是一阵嘻嘻哈哈,大笑不止,大有一副返老还童的天真样儿。于是我想到茫茫人海,可言青春易逝,但感情却是能够永恒。我还依稀记得当年那支意气风发的团首长球队在篮球场上斩关夺隘,与官兵同欢同乐的情形。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又经历了师、军两级班子。时代发生了变化,台上台下的事物和关系亦有了不尽相同的特色。在此细节不再一一赘述。只把我任职师级岗位中的班子成员列表于下,以作历史。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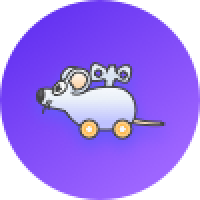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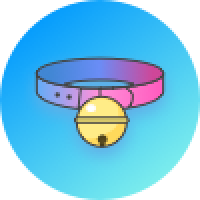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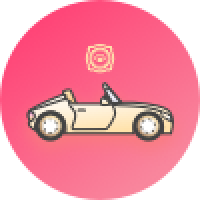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