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森先生的为人亦更是有口皆碑。在全国不知有多少青年书家得到他的关爱、提掖和帮助。他尊长爱幼,在他书桌前一直挂着启功先生的照片,他常说:“启先生为人正直、忠厚、学识渊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炳森先生正义无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某省一青年因装裱书画不慎丢失当地一位极有势力之人的作品,受到无情打击时,他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建议并帮助他用法律的手段得到了应有的保护。他回老家天津市武清县大良乡海自洼村,看到村头的木桥年久失修,给从此过路的20来个村的村民构成很大危险,可政府又无款修缮。于是他毅然找到乡村干部,商议重建新桥的事,并一口承诺修建一座长19米、宽7米的石桥的全部20万元费用,以保此桥50?100年的稳固。在回乡办展与同乡聊天时,得知小学时的老师患了癌症,但因家庭困难,住不起医院动不了手术。他知道后,马上俞往看望,与老师及家人商量手术的事,表示愿意承担全部的医疗费,老人激动得泪流满面而说不出话来,而刘炳森却很真切地说:“父母给了我**,老师给了我灵魂,为老师尽点力是应该的。”第二天一早当炳森先生等驱车去接老师进医院时,全村老少都出来为他们送行。炳森先生还是一个勤奋进取、追求艺术孜孜不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会安排时间很会生活的人。说起他入画时,还有一个小故事。他15岁那年,在天津书店偶然发现一张64开的小画片,是董寿平先生的《沃都云汇图》,画的是黄山天都峰云遮雾锁的景象,那精湛的笔墨、灵动的气韵,深深地迷住了他,为此,贫苦的他第一次放纵自己,花了一毛钱买下那张画片,回来后反复欣赏临摹,并一直保存。无巧不成书,后来董老真的成了他的老师,且不断亲授指点,成为他的良师益友;而那张保存了数十年的小画片,现已传给了他专攻山水的儿子刘学思。“蚊帐利偷读,熄灯写肚皮。庶乎三百草,梦里复依稀。”这是炳森先生在回忆自己下放干校劳动偷临《草字汇》时所作的打油诗。他是一个科班毕业的山水画家,但数十年如一日酷爱书法,那时的他做梦都在临帖练字,也正是这种痴迷,才有现如今的成就和功力。正是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19岁时,便被“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这个名家云集的社团破格吸收为最年轻的社员。几位著名老书法前辈后来看到刘炳森的成就时感慨地说:我们当时没有看错人。1973年深秋的一天,刘炳森应邀出席了一个为欢迎日本书法代表团来访的笔会,日本书家当场命笔,站悬挥毫,好是厉害;而当时我国的书法,只是人、学者、画家的业余技法,皆为伏案作字,这使刘炳森很受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就徒臂凌空的过硬功夫,写出中国人的气派。尔后他每日坚持右手执笔,左手反扣背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到后来他每去日本访问,在众目睽睽之下,左扣右挥,得心应手,日本书家无不感叹叫好。直至今日,刘炳森无论创作篆、隶、楷、行、草任何一体,他都是这样去写,游刃有余。就这一条,恐怕当今书家有此功力者,凤毛麟角;而且,刘炳森在创作之余,一直坚持日课临帖。这许多年,每进他的书房,都可看到床下放着新近临习的一叠又一叠临满各种书体的毛边纸。多年来,为使中国书法艺术发扬光大,扬名世界,炳森先生虽身兼数职,但他还一直承担着为一批来京求学的日本友人上书法课的任务,为了便于沟通,他专心从头开始学习外语,口袋里总装着写满单词的小卡片,利用空闲的一分一秒时间攻读。后来他基本上可以不用翻译就可与日本朋友对话和讲课了。炳森先生不仅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书法大家,他还能诗善画,钻摄影,搞写作,多才多艺。老作家张中行在《潔垣秋草》的序中写道:“如果我有加冠之权,他的帽子就不只书法家一顶,敢加多种冠是源于深知。”刘炳森自己也常说:“书画的后面是学,如果书画家不在学领域里留点痕迹,也将是很大的缺憾。”几年前,他投稿广州一家报社搞的征比赛,一篇《牛年吉日》获奖,他高兴地专程赴广州领奖。他说:“这1000元奖金很有意义,是对我写作的一种认可,要比我在书法上得10万元润笔费还有意思得多。”的确,搞书画只是一个平面,而炳森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立体的多面组合。多年来,他无论出国讲学、访问,还是到各地写生办展,一个沉甸甸的摄影包是他随身必不可少的行李,每次归来都有不小的收获。在朋友们的鼓动下,他从数以万计的底片中,洗出了近200幅世界风景摄影作品,作为出版个人摄影集的准备。作为画家,他懂构图、善捕捉。如只看作品,绝对一个专业摄影家的水平。炳森先生的诗,平仄有章、动情有律、情景交融,他每作一幅山水都要题首自作诗,一位画友拿着他13年前的一幅山水,上面即有诗云:“山上幽居白日暇,云中出没似仙家,烟波浩渺岚光远,异景奇观无际涯。”他同时也喜欢音乐、体育和艺术表演,曾梦想过当音乐家。为了学音乐,他参加过校民族管弦乐队,学过拉二胡、打鼓,为学钢琴,他跑遍书店,为的是搜寻一本尔》钢琴基础教材。他喜爱球类,篮球场上常少不了他的身影。清明,將军又来到这里这里是这座南疆边陲小城边,一处群山环抱中的坟莹。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仍显现出少有的肃穆、庄严。用大理石镶砌的石碑上赫然镌刻着麻栗坡烈士陵园这个曾动彻华夏,如雷贯耳的英雄陵园的园名。今天是清明,将军亦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这里。他今天是从几千里之外繁华的首都来到这里,来到曾经生死与共,如今已长眠于斯的将士们的身边。沉重而雄浑的哀乐在山谷中的坟莹间低徊,将军轻轻抚动端放在烈士墓碑前一尊硕大的祭奠的花环,将军的手在微微的颤抖,将军的眼中早已噙满了泪滴。此刻的将军仿佛听见了当年激战阵地上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厮杀声。当年,将军曾指挥万千雄兵,运筹帷幄,决胜南疆千里。共和国的旗帜上有将军和士兵们共同血染的风采。将军从这里走出去,将军在这里把握住了战争决胜的主动权。如今那场历经近10年的战事早已成为历史。一度被硝烟笼罩的南疆边陲,如今也已是一派宁静和平的气氛。将军的思考早已定格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的辩证:和平是军人的最高追求,战争始终是为军人准备的。没有打不赢的战争,只有打不赢的军队。将军挥泪再一次地和长眠南疆的将士们告别。将军说历史是不可以重写的。历史的结论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生当做豪杰,死义亦鬼雄。历史将永远铭记长眠南疆的英烈们!老友闹话周六下午应一位朋友之邀到一处叫做鼎香园的饭庄聚会。同去的都是一些熟识交往多年的老友。席间大家除了互致问候,还不禁吹些有趣的事。这些场合我因嘴笨,往往只能是好自为之地静坐一隅,洗耳恭听他人高见。我们之中最能侃的当然得数舌压群雄的刘兄、刘老师啦。他是这座省会城市一家学杂志社的编辑,早年从北京大学中系毕业后就在这家杂志社干起了为他人作嫁衣衫的学编辑的行当。我和他相识在云南边境一支边防部队的兵营里。那时他是学编辑,我是喜欢学的业余作者,彼此间谈得拢,加之兴趣相投,于是从这个当时还相当偏僻闭塞的边境之地就开始了我们将近20年的友谊之旅。刘兄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除了才高八斗,酒量也是甚为了得。他虽然现在仍是一介党外之士,官外之员,却始终蕴藏着一股仁人之士的侠肝义胆,遇有不平之事,总会说几句打抱不平的话。当然刘兄还是一位说笑聊天的高手。他朋友多,除了他的为人之外,还有一条恐怕是得益于他的真诚和善言。可想而知当年通过硬考,能读上北大且中系的,如果是没有一点水水,肯定是不行的。有了名牌的基础,加之又多年从事学编辑工作,见多识广,自然善言也就更是情形之中的事了。他讲的笑话可以说得上是东南西北,煎烩炸炒,红黄蓝白,晕素杂陈。听他说笑,你倒还非得多准备几条纸巾不可,否则会笑得你人仰马翻,珠泪纵横而不知所以。而他自己则仍是一副地道的我挨你说的昆明板扎相。我们曾有过多次相聚,但每次他都给人一副生活无忧,神清气爽的欢喜佛态。我真的是很欣赏他的人生状态,得乐且乐,得过且过,自由自在,悠哉、乐哉!我以为像刘兄、刘老师这样一辈子都不曾为官,不曾从商,因而不曾依仗权势、金钱而显赫一时的小小百姓编辑,却能友朋四方来、潇潇洒洒度人生,真是令人击掌,给人启示。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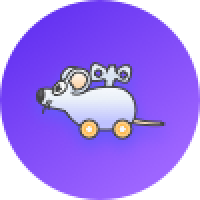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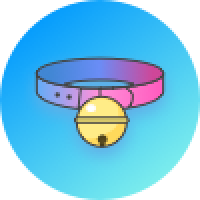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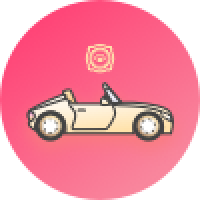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