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席间的另一位老友却又是有另外一种人景况。他是省城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一位副主席,因比我年长,又姓那,故我称他为那兄、那老师。我和他相识是在滇东南的一个壮族苗族自治州。那时我在驻军的部队里履职。他在地区报社的副刊部负责。正值边境有战事,他们亦组织一些反映前线作战的稿子,我也时有他们的约稿,如此一来二往,便多了一些了解,以至后来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那兄老家是云南大理白族中的那氏旺族。几兄弟几乎都是学有所成的化人。在国内散界颇有几分名声的散家那家伦其实就是那兄之亲兄。大概是家学的影响,养成了那兄外柔内刚的性格。他早年从云南师大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砚山县的一所中学教书,教学之余开始搞小说、散之类的学创作,有时还写点花灯、话剧什么的。几经苦斗,终成大器。进而被选调到了州里的报社做了副刊编辑,后来又被选升到了《含笑花》做了主编,当上了州联主席、最后又重用到省里执掌了省联副主席的帅印。看到那兄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想除了他的学识,还主要得益于他的为人。那兄是一个忍性极高而又不善权术的人,虽然学识、悟性甚佳,但在那人相轻、复杂得可以的圈子里,却是久久地未能神清气爽过来。说来说去他以为还是那官场惹的火。近日在昆,偶有小聚,说起为官,不禁唏嘘:宦海无边,何时才能回头!于此,我也只能表示理解和同情,不由也生出一声感叹:真是高处不胜寒啊!席间的另一位则是刚认识的一位新友,他就是这家鼎香园饭庄的老总,姓杨。他说依一冋生二回熟的理论而言我们也算是老友了。席间他不时过来敬酒,也说一些笑话逗乐。他说在他这个饭庄真正的老板其实是他那个才刚刚上小学的儿子。为什么?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不是称我老婆为老板娘吗?如果我成了老板,岂不是要叫我老婆为妈了。所以说儿子是老板才是拨乱反正了的硬道理。经他这一说倒是感到了一些新意。老总自嘲自己不过是这个饭庄的高级打工崽,所挣之钱都是给儿子老板和老板娘花的。此言一出不禁使人生出几分凉意来!真想不到一个看似多么粗俗的农民老板竟然把一个人世间如此传宗接代,物质不灭,周而复始的理论透析得如此通俗了然!我在想活在世上的人们啊,何时才能打破金钱的伽锁,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是不是真正是如马克思老祖宗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诚实是命当我拟好这篇章的标题的时候,我还一直在犹豫应不应该把诚实放上如此沉重的天秤。然而曾经发生在我身边,对我震动和影响很大的本来很普通的两件事,仍然促使我把这篇章的标题定下来,并把这篇章写下去。这个人是曾经同我一起共事的同事。论才华,水平应该是堪称一流的。他是贵州山区的人。靠自己的勤奋在一个级别不低的机关里谋到了一个级别不低的职位。同样也是靠他自己的勤奋在领导和同事中有很好的口碑。应该说同样是靠他自己的勤奋仕途是一片灿烂辉煌,前程似锦,还有着谋取升迁更高职位的机遇。他本来是一个不事张扬,比较低调的人,因此在机关里常常只能见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一段时间机关里同时传出两条消息,一条是他所在部门的主要领导空缺了,他很可能作为人选提升顶替到这个位置。另一条是有一天他突然间在办公室晕倒,送进了医院的抢救室。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个空缺的位置最终还是选了不是他的新人。而他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终于不幸辞世。听说是肝硬化晚期。据医生和他的家人讲他这个病早就有了,他自己也是明白的。如果不耽误早期治疗,恐怕还多有几线生机。但他却在做官与要命上失衡了。特别是在那个领导位子空缺期间他还特意向医生提出提前出院的请求,同时要求医生一定要对他的病情保密。事后,我总在想人都到了保命的份上,怎么还在想那个多么不应该想的,而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生命健康的问题。一个人诚实做人了一辈子,而却在这个关键的坎上忽悠了自己,最终还是很不值得地带着不幸和遗憾离去。我要说的另一件事的主人公几乎与上一件事中的主人公有相同的情形。他已是一个担当了相当职位的干部。但他也没有逃脱疾病给他带来的厄运。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发现脑干上长了个米粒大的瘤子。医生告诉了他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却没有听医生的,同时还把这个病情严密地封锁起来。原因是那时上级正在进行干部考核。他自然也是考核中的重点对象,有希望成为提升又一个更重要职务的机遇。上级的考核结束了,他亦顺理成章地走马上任到一个更高级别的职务。然而就在他履任新职仅只七天,脑病恶化,被确定为恶性胶质瘤晚期。虽经努力,终是无力回天,亦不幸因病离别尘世。记忆中的这两件事,几乎都出于同一个考量,拒绝了诚实对待自己。在做官与要命这个本来不难权衡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衡,最后毕竟是导致了悲剧过早的发生。当然人活在世上或许都可能会有很多的**,但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上,的确不能糊涂了自己。诚实对待别人,也诚实地对待自己,这应该说也是人生的一条要义。诚实是命恐怕不是危言,而是真理。于是我拟定了这个作的题目,写下了这篇做人的小。但愿中所述,只是个案,只是过去。艾教员一直以来在我心中有一个让我十分尊敬和崇拜的人。他不是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亦不是身居显位的达官。而是如他自诩的,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姓艾名思奇的教员。当然直到现在,我都并没有真正见过这位艾教员。我认识他是在一处图书馆的书架上偶然看到一本书名为《a众哲学》的书。作者就是这位叫艾思奇的人。这本书装祯得很普通,与现在那些装祯得华贵十足的书相比甚至还显得有些土气。那时我正读初中一年级,偶然看到这个书名感到很特别,那时我真的还不懂哲学为何物。但出于好奇我还是硬着头皮抱着书翻了几页,没想到书中那简单通俗的字竟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书中说的既有我感到陌生不解的东西,也有我感到似乎就发生在身边的熟悉的东西。我开始以一个小小初中学生的水平去读着这本书。后来到了高中,我遇到了一位亦曾经在中央党校工作过的叫胥思海的政治课教员,我捧着这本书向他请教,他饶有幸味地给我谈起了这本书,谈起了书的作者艾思奇。如此,便知道了艾思奇是云南人,同时亦是被**主席称之为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所撰著的《伏众哲学》这本书一直是一本影响很大的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的重要地位。从那时起,在我还非常年轻的心灵里就有了对艾思奇先生十分尊敬和崇拜的英雄情结。我也一直把我后来在新华书店购买的这本叫《汰众哲学》的书带在身边,百读不厌。其实艾思奇先生在我年岁尚小的时候,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但对艾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却有着一份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崇敬之情。那是在今年的三月上旬,我有了一次去艾先生的家乡云南腾冲的机会。那天我在一位腾冲友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侨乡和顺艾思奇的故居。故居里摆放着艾先生生前的遗物,而那本书名为《汰众哲学》的书被摆放在很显眼的位置。我不由自主地久久地伫立在这本书摆放的桌前,心中油然升起对故人深深地怀念之情。同时,也不由记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篇发表在一家地方报刊上,题名是《我还是艾教员》的章。章记述了身为党内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的艾先生,一次到中南海的怀仁堂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一些熟识的已经在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的战友和同事在见面聊天之后便问及艾先生现在在干什么,言外之意,凭他的学识和能力,他也一定担任了重要职务。但艾先生却十分坦然和平静地告诉他们:我还是艾教员。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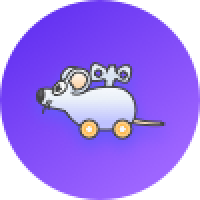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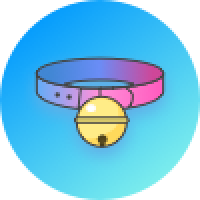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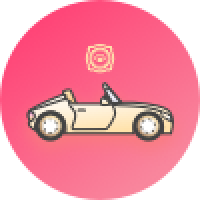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