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艾教员。”这一既朴素实在又掷地有声的回答,折射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于山的磊落胸怀。的确艾先生把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信仰都放到了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业上,直至他逝世,都还是一名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堂上的教员。他任过的最高职务也只是代理过河南省开封地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可是他的学识和人品却永远令世人敬仰。他的生命就如那本《汰众哲学》的书一样永远光彩夺目,彪柄千秋!他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应该很多很多。在读书中学做人人生几十年,一直有一个喜欢读书’特别是读励志类书籍的爱好。而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亦使我深深悟出了在读书中学做人的道理。其中让我体会最深的有这么一段难忘的往事。那是在199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那时我在老山前线某守备师任政治部主任。一天,收到来自昆明的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位比较熟识的叫辛勤的编辑朋友的来信。他在信中谈到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在全国发行的少儿刊物《蜜蜂报》正筹办一个《学做人》专栏。特别邀请我作为专栏作者专门定期为该专栏撰写一批章。我收到他们的邀请一方面感到很高兴、很荣幸,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应该说在这之前我已写作和发表过不少的学作品和其他章,并拥有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头衔,做这样的事不会太难。但作为特约专栏作者于我来说毕竟还是第一次,且写作周期快,要求高,加之我又军务在身,亦同时感到任务并不轻松。最后还是为出版社的热诚相约和《学做人》这个有着特别教育意义专栏的吸引,而愉快地接受了写专栏的任务。因《学做人》专栏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少年,章要求小中见大、形象生动有故事性,有教育意义。因此,我在平时读书的积累中,又开始了较为集中的新一轮的阅读。我是军人出身,我自然一向崇拜那些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开国将帅们,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的经历及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于是我把我读书写作《学做人》专栏章的重点就首先定在了编写开国将帅们鲜为人知,却又富于传奇色彩,励志做人的小故事上。我从出版社借来了由当时海燕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出版的10大将传记丛书和其他一些关于开国将帅的书籍,共计约200余万字的篇幅。为了写好每一篇《学做人》的章。我在公务之余全身心地投入了几百万字的书籍的阅读中,在浩繁的字中去寻觅和体会那些与我心灵的共鸣。可以说这10多本书中的每一本书中所记述的将帅们的故事都给了我心灵深处深深地激动和震撼,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丰碑,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做人的一面旗帜。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并结合专栏章的要求,我着手编写了《一张作战图的故事》——刘伯承元帅的故事;《彭总的零用钱)彭德怀元帅的故事;《元帅的风格》朱德、贺龙、陈毅元帅的故事;《比刀术》——叶剑英元帅的故事;《乐天派将军》——陈赓大将的故事;《这个角儿我来演》——罗瑞卿大将的故事;《黄师长分梨》——黄克诚大将的故事;《是水硬还是石头硬》——张云逸大将的故事;《取长补短》谭政大将的故事;《补苗》——王树声大将的故事;《戒酒》——徐海东大将的故事;《不能骂人》——肖劲光大将的故事;等等数篇稿。我把我的真情实感都融入了这些稿中,我要把他们做人,行事的高尚人格和品质讲给我自己,同时也讲给青少年朋友们,以成为我们做人、行事的榜样和楷模,激励并惠及我们一生。我在编写这些小故事中,也同时一一写下了我的心得体会,也可以说是我在读书中学做人交出的一份答卷。我在《一张作战图的故事》中就这样写道:中国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刘伯承元帅一生治军很严,是一个最讲认真的人。他在发现部属因为不认真而标错地图的时候,就用数楼梯这样一个形象而风趣的比拟来启发部属对办事必须认真的认识,特别是对自己觉得已经十分熟悉的事物,也不能马虎疏忽。一个人只有从小乃至一生都像刘元帅那样养成讲认真的习惯,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在学习上、工作上和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我在《戒酒》中这样写道:徐海东将军在早年参加革命任自卫军大队长时曾因多喝了酒而错怪并体罚了战士,心中感到很内疚。从此下决心戒掉了从十二岁当窑匠时就学会喝酒的多年的习惯。这充分体现了徐将军严以律己的高尚人格和坚强毅力。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在自己的人生和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嗜好和习惯。但当这些嗜好和习惯影响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时,我们也应该像徐海东将军那样下决心把它戒除掉。这样做不仅能培养我们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也有利于培养我们高尚的人格。当然,我在其他的稿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将帅们故事所给予我的教育和启示。正因为有这样的读书感悟,所以《学做人》这个栏目做得有声有色,受到了社会和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广泛好评。并同时受到了团中央、全国少工委的表彰和奖励。于是我始终坚定的认为,在读书中学做人应该成为我们热爱读书的一种高尚精神境界和追求。书稿风波当我把刚刚出版的《後石恋》这本小书捧献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的心绪竟然显得是那样地难于平静,犹如一粒彩色的小石子不小心掉进了这原本是平静、明彻的心湖里。这之中既有某种成功者在获得成功后的激动和欢悦,同时更有着某种成功者在成功体验后随之袭来的深深地不安和惶惑。哲人说:学的事业总是充满荆棘,留下遗憾的事业。此时此刻我仿佛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要义和个中滋味。我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与学相识并结下不解之缘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多雪的冬天,滇西北雪山高原深处那座叫做中甸的小县城边的一个藏族连队里来了一位省城某出版社的女编辑。她是带着编写一本反映藏族翻身农奴家史书籍的任务来到这里组稿的。到了团里,团里宣传部门的同志给她介绍,能集中反映翻身农奴家史的主要是藏三连和藏七连。七连的有利条件是,他们那个连队刚从内地一所大学里分配来一名当兵锻炼的大学生,写家史的任务可以交给他去完成。于是这位女编辑便选择了七连,具体写作的事也就交给了这个可以承担写作任务的大学生。当然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兼有当兵接受改造、接受再教育身份的“臭老九”,能领衔做这份工作,也实实在在是难得的一份殊荣。于是,我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真诚和执著极其投入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利用当兵改造之余和连队给我安排相对机动一点的时间开始了收集材料和写作的工作。我通过了解,选择写作的对象是这个连队的二排长知批。知批排长的特殊生活经历深深触动了我。他出生不久,阿爸、阿妈便因为疾病相继去世。在他不到五岁的时候便被送进喇嘛寺里当了一名小喇嘛,一直到17岁参军前做了10多年的小喇嘛。小喇嘛的生活是极其艰辛的。他小小的年纪,却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到离喇嘛寺很远的山谷深处的水沟里去背水。背回来的水还要负责一桶一桶地装满寺庙中大大小小的几十个佛坛里。而吃的却是用来喂牲口的粘粑面调成的稀糊糊。稍不遂意还要遭受大喇嘛们的责骂和毒打。正是根据他的这一段少有人经历过的苦难生活,我写成了?、喇嘛的血泪史》。稿子写成后交到团里,团里宣传部门的头头认为写得真实感人,稿子便由团里寄到了省城的那家出版社,那位女编辑的手里。不久,我便收到了女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对这篇稿做了诸多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核实和充实的意见。信写得很亲切也很鼓舞人,使我这个第一次提笔为出版社出书写稿的人,感到了莫大的荣幸。于是我便按照出版社的意见,对原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稿子改成后,我又按团里意思直接把稿子寄到了省城出版社。我天天都盼着稿子用出的回音。不想几个月过去了,一天团里的王干事来到连队找到我,我向他问及稿子的事。他带着阴郁的神情告诉我:你闯下大祸了,上头政治部追下来,责问团里是谁叫写的稿子,为什么不经上面政治部的批准。正是“革”的年代,人们对政治的东西都十分地**。写稿本来是团里宣传部门同意的,何况写的是翻身农奴战士的家史,大方向不错。但现在上面追査得很厉害,如何交代?团里宣传部门只好硬着头皮应付上面说,是团里同意的,与作者没什么关系。我这才算是勉强过了关。那时候政治气候就是如此。这场不大不小的写稿风波总算平息了,我这也算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政治风浪袭来的个中滋味。这件事也一直深埋在了我的心底,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调到了上级机关,同了解内情的同事谈起来,才知道了一点真相。原来是一位在机关拿笔杆多年,成天总想出名,而又一直未能如愿,对人家能写点东西总是妒嫉得要死的人,在不明真情的领导面前制造的一起冤案。这个人据说就因为干了好几起这方面的事,最后总算是被领导察觉,把他做了安排转业的处理。联想起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真可谓是千人千面、人间百态,也没有什么太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但这件事确实对我教育启发很深。常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似乎是有点不言而喻的。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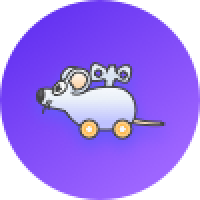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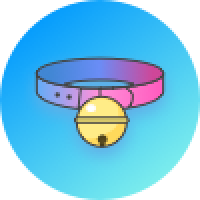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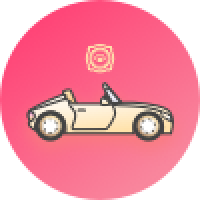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