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确实还没有走远,他跟两个随从刚刚沿水路走到了丰城,就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宁王叛乱了。随从们十分慌乱,王守仁却并不吃惊,他早就知道这一天必定会来临。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还是显得那么残酷。孙燧,想必你已经以身殉国了吧。王守仁仰望着天空,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同乡好友了。但还没等悲痛发泄完,他就意识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马上停船靠岸。”王守仁下达了命令。随从以为他要去办事,便紧跟着他上了岸。可是他们跟着这位仁兄转了好几个弯子,也没见他去衙门,却又绕回了江边,另外找到了一艘小船,继续由水路前进。这是演的哪一出?“宁王是不会放过我的,他必已派人沿江而下追过来了,陆路太危险,是不能走的,刚才我们上岸,不久后我们走陆路的消息就会传开,足以引开追兵,而我们的船是官船,目标太大,换乘小船自然安全得多。”随从们呆若木鸡地看着平静的王守仁。真是个老狐狸啊!玩了一招调虎离山计的王守仁并没能高兴多久,因为他面临的,是真正的绝境。宁王叛乱了,孙燧等人应该已经遇害,南昌也已落入叛军之手,而且这位王爷想造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整个江西都安置了他的势力,许多地方随同反叛,情况已完全失去控制。虽然有巡抚头衔,旗牌在手,但就目前这个状况,坐着小船在江里面四处晃悠,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外面治安又乱,一上岸没准就被哪个劫道的给黑了,那还不如留在南昌挨一刀,算是“英勇就义”,好歹还能追认个“忠烈”之类的头衔。那还有谁可以指望呢?兵部?王琼是老上级,应该会来的,不过等到地方上报兵部,兵部上报内阁,内阁上报皇帝(希望能找得到),估计等到出兵,宁王已经在南京登基了。内阁也不能指望,且不说那个和宁王有猫腻的人会如何反应,自己好歹也在机关混了这么对多年,按照他们那个效率,赶来时也就能帮自己收个尸。朱厚照?打住,就此打住,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算了吧。没有指望、没有援兵、没有希望。满怀悲愤的王守仁终于发现,除了脚下的这条破船外,他已经一无所有。黑夜降临了,整个江面慢慢地被黑暗完全笼罩,除了船上的那一点灯火外,四周已经是一片漆黑。王守仁仍然站立在船头,直视着这一片阴森的黑暗。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孙燧已经死了,宁王已经反了,那又如何?又能怎样!心学再高深,韬略再精通,没有兵,没有武器,我什么都做不了。事情就这样了吗,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头过去再说?那孙燧呢,就这样白死了吗?王守仁并不喜欢朱厚照,也不喜欢那群死板的文官,但他更不喜欢那个以此为名,造反作乱的宁王。他痛恨践踏人命的暴力,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人性是最为根本的一切,是这个世界的本原,而这位打着正义旗号的宁王起兵谋反,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不过是为了他的野心,为了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打倒当权者的宁王,将是另一个当权者。唯一的牺牲品,只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当政,他们都将是永远的受害者。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去拿纸墨来。”王守仁大声说道。随从们从行李中拿出了笔墨,递到了他的面前。那一夜,王守仁没有睡觉,他伏在书案前,彻夜奋笔疾书,他要写尽他的悲痛和愤怒。第二天一早,随从们发现了散落满地的纸张,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所有的纸上都只写下了四个醒目大字:誓死报国。一夜未眠的王守仁依然站在船头,对他的随从们下达了最后的指令:“等到船只靠岸时,你们就各自离去吧,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了。”随从们对视了一眼:“那王大人你呢?”“我要去临江府。”临江府,位于洪都下游,依江而建,距离洪都仅有二百余里,时刻可能被宁王攻陷,是极为凶险的地方。“王大人,临江很危险,你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王守仁笑了:“不用了,你们走吧,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随从们不是白痴,他们都知道王守仁要做的那件事情叫做平叛。于是他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王大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王守仁收起了笑容,严肃地看着他们:“我一个人就够了。”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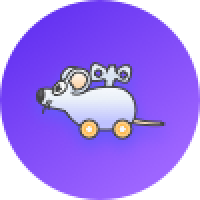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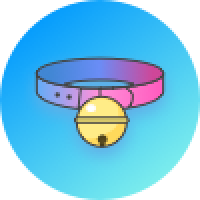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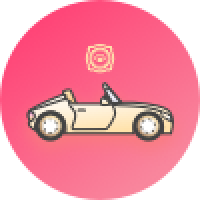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