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写给张爱玲女士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当我合上这卷书的时候,穿过岁月照亮过往的光息灭了,没有了张,也看不见他们——他们已经像影子一样消失了,一如过去的所有被忘记了名字的人们,一如他们从来不曾来到人间。”读过很多遍这句话,每次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感慨。于是我也常常会在脑海中极力搜索那些“一如他们不曾来到过我的生活”中的人。我终于翻出了许许多多在我脑海中若隐若现的影子。有些隐约能记起丁点音容笑貌,然而到底是模糊了,模糊得就如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在水里浸过很多天一样,模糊到怀疑他们到底是我现实中认识的,还是在某部影视小说作品中看到过的。可有一些人,不曾想起他们时以为是淡忘了,当再想起时却是愈记愈鲜明,原来小小内心世界一直有他们的印记,一直有他们的一席之地。Jun便是其中一位。Jun是我读书时的同窗至友,虽然多年未联系,我却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Jun年长我三岁,是家中独子,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他一向比较成熟稳重,也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他在言语间总会渗杂些苛刻,所以在同学之中有些孤立。但我们却挺合得来。我是一个非常顽皮、活泼好动的女生。记得那时因为家远,双休许多同学都不回家。因为年纪小,都不参与校外那多姿多彩的生活,周末便常呆在教室里看电视或学习。Jun喜欢看书、写作,在校刊上发表过数篇小作。我则喜欢说话,声音又响亮,常常在教室里旁若无人地喧哗。没有听众了,即便Jun紧握笔头冥思苦想之际,我也会毫不客气坐到他面前海阔天空一吐为快。偶尔他会说:“你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歇会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合格的听众。Jun也常常劝我动手写,说他可以帮我修改。在他的鼓励下我倒也略有小成就,在校刊上也继续发了几个小豆腐块。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他鼓励我一直写下去,说一定会越写越好的。然后我到底是让他失望了。毕业以后我除了工作,便是麻将、逛街,直到后来的相夫教子,再无心笔长笔短了。记得在师三时,Jun告诉我他在写一篇以我们班集体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我问他里面有不有我,能不能给我瞧一眼。他说有我,但要到完稿时再给我看。后来我经不起好奇,趁他不在,偷偷翻过他的抽屉,找得几页残稿,真的在里面看到了自己,把我写得也让我挺满意。后来再问起他小说的进程,他只是笑笑。然而直到毕业我再没看到他的残稿及定稿了。不知不觉中便到了毕业之际,Jun在我的留言册上写到:“……希望有一天我能到南昌看到一枝成熟、美丽的梅!”只是,毕业后一晃数年,他再也没了音讯。毕业后曾托同学打听Jun的消息,却鲜有人知,他没有与什么同学有密切的往来。毕业一年聚、三年聚、五年聚,他均未参加。有个同学说集体学习时曾遇到过和Jun在一个镇工作的同行,问及Jun,同行说他为人处事挺尖锐,便没有后话。我又想起我曾偷看他底稿的那一刻,他的字,苍劲有力,锋芒毕露,一如他的性格一样锋利得刺人,不善变通。至此,我那颗一直希望他过得安稳的心,又多了一份忧虑。在人生旅途中,像Jun这样让我念念不忘的、牵挂的人很多。在这个连感情也不能相信的年代,更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异性之间还存有纯友情。但请不要用恶俗的眼光批屑我们。Jun于我,是同窗,是至友,一如在远方工作多年不曾见面在心里一直惦念的兄长。我无他求,只希望Jun和所有我牵挂的人都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们能像我在心里念叨着他们一样念叨着我……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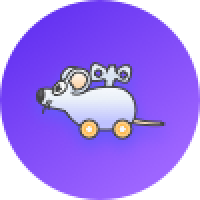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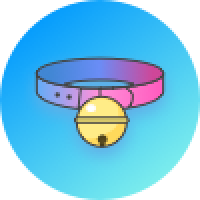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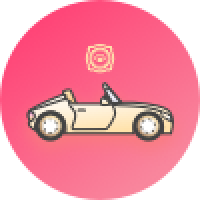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